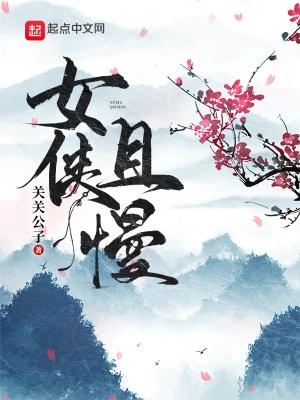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对弈江山全本txt > 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章华夏好男儿岂能侍豺狼(第3页)
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章华夏好男儿岂能侍豺狼(第3页)
可一位老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看过曾祖母的笑容吗?”
学生们纷纷点头,打开晶石投影,播放高清影像。
老教授又问:“那你记得她做饭时哼的那首歌吗?记得她摸你头时手掌的温度吗?记得她说‘乖乖吃饭’时那种语气吗?”
教室陷入沉默。
最后,一个女孩低声说:“我不记得了……影像里没有这些。”
老人轻叹:“技术可以复制画面,却无法复制感受。真正的记忆,不在眼里,而在心里。”
于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重新走进忆学堂,学习如何用心记住一个人,而不是靠机器储存。
他们学会在饭桌上听长辈讲故事;
学会把祖母的药方抄在纸上,亲手熬一次苦汤;
学会在清明时节,不去扫描墓碑二维码,而是蹲下来,用手擦去石上的灰尘,然后轻声说:“我来看你了。”
这个世界越来越快,可总有一些人,愿意慢下来,去记得。
某日,考古队在极北冰原发掘出一座远古城池遗址。城墙由黑石砌成,街道布局奇特,所有房屋门窗皆朝南方。最令人震惊的是,城中心有一座巨大圆形祭坛,地面镶嵌着数千枚铜铃残片,排列成一幅完整地图??正是当年木铃最初铸造之地的倒影。
而在祭坛正中央,立着一块无字碑。
科学家用尽手段也无法解读其材质,红外扫描却发现碑体内部蕴藏着极其复杂的能量波动,频率与人类脑波中的“思念波段”完全吻合。
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将其移走研究。投票前夕,一位来自桃林村的老妇人站了出来。她是沈眠邻居的曾孙女,年逾九十,拄着拐杖,声音却坚定:
“不要动它。这不是遗迹,是心跳。”
会议最终决定:原地保护,列为禁区,永不开发。
多年后,每年春分,当地居民都会远远看见,那块无字碑上浮现出淡淡的光影,像是一行行流动的文字,又像是一首无声的歌。没人能看清内容,但每个看到的人,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安宁,仿佛听见了久违的呼唤。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小男孩在放学路上摔倒了,膝盖流血。母亲扶他回家,一边包扎一边轻声哼歌。男孩忽然抬头问:“妈妈,这首歌是谁教你的?”
母亲想了想:“外婆教我的。她说,是她小时候,外曾祖母在灯下缝衣服时唱的。”
男孩眨眨眼:“那她们现在还能听见吗?”
母亲停下动作,望向窗外飘动的风铃,柔声道:“只要我们还在唱,她们就一直听得见。”
春风穿堂而过,铃声叮咚,清脆悠扬。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
而在所有响起铃声的地方,无论是屋檐下、山谷中、海岛旁、还是城市高楼之间,总有那么一些人,微微仰头,嘴角浮现浅笑。
他们什么也没说。
但他们心里清楚:
她还在。
她们都在。
只要还有人愿意轻轻说一句“我记得”,
那些离去的身影,就会穿越光阴的迷雾,再一次,温柔地回到我们身边。
铃声不止,因爱未断。
归途漫长,幸有守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