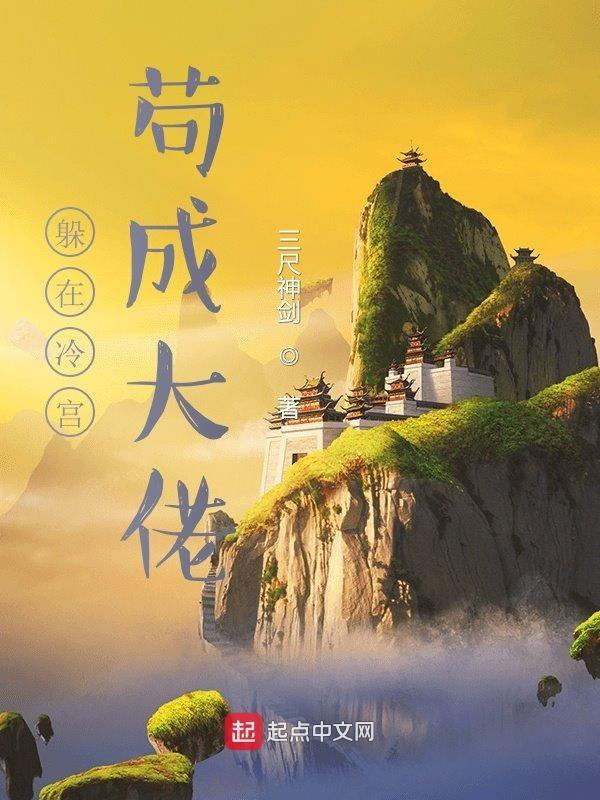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长恨歌原文 > 第135章 维护(第2页)
第135章 维护(第2页)
“忠武堂?”余惊秋道。
陆元定说道:“许是那忠武堂的端了杏花天,拔除了许州城这飞花盟的爪牙,鼓舞了士气,想要趁此机会,一举深入。我们只怕也要派人去一趟。”
余惊秋皱眉,没有应声。云瑶和杏花天先后出事都与忠武堂有关,即便是忠武堂所做以正道名门的角度来看没什么不妥,她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怪异感,仿佛叶藏于林,有什么微末的细节被她忽略了过去。
吴青天思忖道:“虽说楼彦作乱,宗内伤了元气,但上次楼彦邀请各路人士,是以干元宗的名义,忠武堂定力支持。这一次换做忠武堂做东道主,我们出于情面,还是得出面。最好是你出面,你接任宗主之位后,一直在宗内,鲜少见外人,也时候出面让别人认识认识我们干元宗的新宗主。”
余惊秋回过神来,点了点头,“那就按师叔说的,我去一趟。”
余惊秋从祠堂回来,已是晌午。
深秋的太阳暖意融融,照耀得人毛孔舒张。
几日前的动乱里,楼彦的人下手偷袭,不少长老负伤,得亏韫玉和月牙儿在,这对妙手回春的师徒是不幸中的万幸,没让宗内损失扩大。
长老们伤势稳定了下来,韫玉也回来水榭歇口气。
余惊秋到水榭前时,远远地就瞧见屋内的师徒俩在争执。
“我为什么不能见他?”月牙儿高声问道。
“那小子不是好人。”韫玉沉着一张脸。
月牙儿从没想过自己师父也有不可理喻的一天,“春庭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比师父清楚。”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师父是不是还要说,你比我年长,见过的人比我多,更懂识人?”
“月牙儿……”
月牙儿鼻子一酸,她情绪来得太快,“不要叫我月牙儿,我不想你叫我月牙儿!我已经成人了,你不要总把我当孩子看待!”
中秋灯会时,月牙儿在心中承认了忘不了韫玉的事实,正自怅惘无措时,韫玉在她危急之时出现令她欢喜,可这欢喜在韫玉待她的态度一如往常,让她想起离谷的初衷时,这份重逢的喜悦荡然无存。
师徒重逢,这不是慰藉相思,这是饮鸩止渴。
月牙儿自灯会回来后,只见过春庭一次。那夜春庭回来的晚,知道宗里发生的事后,担忧她的安危,赶忙来见她,见她安好才放下了心,再度为自己的冒昧道歉。月牙儿也向他道歉,她明白了自己的心,再不能和他深入下去。
韫玉不知,月牙儿实际上已经疏远了春庭。
月牙儿不知,原来有时候成不了情人,见面会彼此尴尬,连朋友也难做。
月牙儿自觉得给了春庭期望,却无法做到善始善终,本就愧疚难受,偏生韫玉在她耳边念叨,不许她和春庭亲近。她不会和春庭亲近,这早已是一个必然的事,原因正是这唠叨的人,这实在令她郁闷气结。
韫玉沉默许久,声气放软了些,“师父不是要拦着你喜欢谁,和谁相交,只是那小子不是良人。”
“春庭怎么不是良人?”月牙儿痛苦,也不想顺着韫玉的意,令她太痛快,因而和韫玉反着来。
“他太年轻。”
“和我年纪相仿。”
“他没有根基,没有建树,护佑不了你。”
“天资卓逸,未来可期,干元宗是他的后盾。”
韫玉说一句,月牙儿驳一句,竟是十分维护春庭,韫玉火气上来,“他轻浮!大庭广众之下吻你!”
“他已向我赔罪,也向他师父告罪,领了责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相信他以后会更好,更稳重些。”
月牙儿见韫玉咬着牙关,沉着眉峰,不待见春庭,不赞许她喜欢他,心里蓦地一动,有个念头转动,生出一点期许来,她直视着韫玉双目,试探道:“我要是一定要同春庭在一起,师父想要怎么处置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