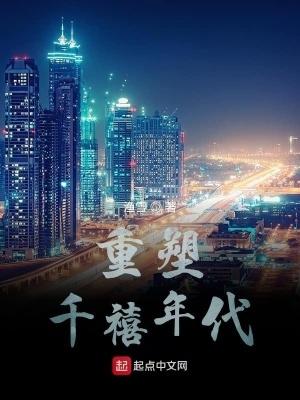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归义非唐TXT百度分享 > 第524章 政通人和(第2页)
第524章 政通人和(第2页)
尽管不见店铺,却能从那些声音中感受到疏勒的热闹,令人忍不住询问道:“不是说疏勒都是回鹘人吗?”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老卒爽朗笑道:
“如今的至尊将胡人迁往西州和河西,将关东的降卒和其亲眷迁徙而来,去年入秋又陆续迁徙来了几千逆民,这疏勒如今便以某汉人居多了。”
“城内有三千户戍兵和两千多屯户,城外那些耕地基本都是他们的。”
“尔等要下乡的地方,大多都在赤河的南边和西边。”
“疏勒镇在南边和西边设了两个屯田折冲府,起码有上万人在南边复垦。”
“他们与尔等不同,尔等官学出身的学子,干活都是把好手,他们不行。”
“这些中原来的人虽然有学识,但不知如何耕种,也不知道如何掘井、挖渠。”
“某等人手不足,不然也不会将汝等从龟兹抽调到疏勒来。”
在老卒一边驾车一边解释下,众少年人们也知道了自己此次下乡的地方情况。
在他们还在沉思时,几辆牛车已经来到了疏勒镇的牙门处。
十余名老卒下车将牛车拴在下马石上,紧接着去牙门与牙门的将士交涉。
不多时,领头的老卒便示意少年人们跟他走入牙门之中,而其余的老卒则是去牙门的大庖厨吃饭去了。
疏勒镇的牙门并不小,占地足有十余亩,老卒一边走一边与众人介绍疏勒镇和中原州县的不同。
“虽说南疆的胡杂都被敦煌王率军清理了个干净,南边的于阗和仲云也有都护府的派去的驻兵,但这南疆还是有不少小部落在游牧。”
“他们虽说都是都护府治下的百姓,但有些时候也会化身盗寇去劫掠来往商旅。”
“汝等下乡后,虽说屯田折冲府内也有战兵负责巡视官道,但牙门担心巡察,百姓可以带弓箭与短兵、大棒防身。”
“这疏勒镇内的事情,都由斛斯都尉掌管,斛斯都尉下设节制兵马的三名别将,以及负责政务的录事参军、仓曹参军、兵曹参军和甲胄参军,以及都护府派遣的监军使和负责管理屯田折冲府屯田的营田使。”
“汝等下乡后,多半是与营田使打招呼最多。”
“这营田使半个月前才赴任,也是临州狄道人,与你们之中有一人还是同乡,说不定会好好照顾你们。”
老卒说着,少年人们也跟着他来到了写有“营田”的一处院子前。
院门前的两名兵卒见到他们,立马便戒备了起来,而老卒则是带着鱼符和军碟走了上去。
经过检查后,其中一名兵卒便带着他们走入院子中。
院子占地不小,简直就是个缩小的县衙,光前院就有亩许。
“龟兹镇第二营第三团第三旅第二队队正赵越,奉郑都尉令,将官学下乡学子护送至疏勒,请营田使勘合。”
老卒带着他们穿过院内戒石坊,随后来到正堂外作揖,少年人们也纷纷作揖。
“正堂内坐着左右十余名军吏,主位则是身穿浅绿色官袍,相貌周正的短须主官。”
见到来人,主官好似松了口气,同时示意他们走入堂内。
十余人走入堂内,接着便见到有军吏接过老卒手中鱼符与军碟,勘合属实后还回。
那主官目光在众人身上打转,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队伍中身材堪称高大,却又皮肤黢黑的少年人身上。
虽然不过十五六岁,可少年人身长五尺六七寸,便是放在及冠成人中也算得上中上,更别提在这群少年人堆里的。
其肤色虽黢黑,但仪表周正,风神爽拔,如鹤立鸡群之中,格外引人注目。
“此少年人倒是生得好仪表,不知唤何姓名?”
“回禀营田使,某唤曹远仁。”
少年人不卑不亢说着,主官闻言立马浮现笑容,接着看向身旁的军吏。
军吏微微颔首,随后带着几名军吏离去,不多时带着许多兵器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