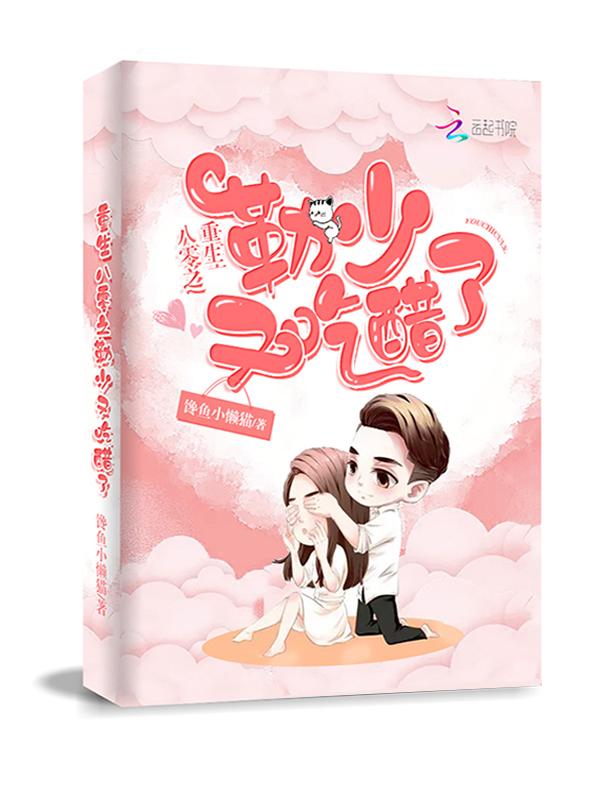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心脏病下病危通知书还能活多久? > 第 73 章(第1页)
第 73 章(第1页)
梦,她永远离不开的梦。
一望无际的海,在阴沉的天幕下轻轻晃荡。
而她在一只小船上醒来,对面坐着一个戴着黑色兜帽的人,西凌微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清他的神色,但就笃定对面坐是一个女生。
那人见西凌微醒来,默默伸出了一只手,西凌微无视了她的友好,摸着船沿,看向海的远方。
不出一会儿,她便听到从船底传来笃笃笃的声音,像有人下楼梯,又像有人在黑漆漆的地下室用头顶撞门,西凌微的脑海里依次浮现这两个阴暗的场景,最后没忍住打了一个寒颤。
对面那人见她冷,脱掉了黑色斗篷,递给了她。
大雾横在二人中央,船被海水拍得咿呀低吟。
西凌微接过黑斗篷,披在背上,顿觉沉重。她想把黑色斗篷脱下来,但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在她起身想朝递给自己斗篷那人走去时,她悚然发现,静静在大雾中打着旋的船上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一种被遗弃的孤独紧裹着她,让她不由地后退了一步。下一秒,她就踩上一根木棍摔了一跤——身体咔擦一声撞坏了船底。
她心一紧,而预料中的疼痛却没有感到,只模糊摸着那根颇有重量的木棍,借着微光抬起,被那锃亮的内凹刀刃吓得一悚。
这比此刻纯黑天幕里弯得诡异的月亮还要令人胆战心惊。
一股不知何处而来的凉风吹着她身体,她伸手掀开自己黑袍,在看到船底连接的那空洞阴森的楼梯时一种强烈逃出去的欲望引诱着她。她在逼人寒气中慢慢踏下一级台阶。
没有到来的失重感让她松一口气,就在她想下第三极时,涂在楼梯上黏黏的东西扯着她的脚底。
她低头一看,那楼梯却干净得几乎能反光。而再动脚时,又发现那粘腻感不过是错觉。
她不在意,举着内凹长杆弯刀,踏下楼梯来到了一道看不到尽头的阴暗长廊。长廊两旁是一扇又一扇紧闭的小门,各门上挂着不同的门牌,有些是一些可怕的虫子野兽,有些门牌上是一滴血,还有的则是一栋轰然倒塌的大楼。
她一直往前走,每当在一扇门前停下时,都能透过门清晰地看到屋内发生的事。尖叫、呜咽,刀下的凶杀、救不活的人,妻离子散、老死空房,偷走同桌的钱袋、被歹徒割掉耳鼻眼……每一扇房间里都是恐惧,不同的主角,无一例外地卑劣。
她继续走着,见到玻璃门框一晃而过死神的倒影。
那是她。她讨厌扮演各种角色。就在她不想偷窥别人梦境而回头时,走廊前一个肤色惨白的小孩将她吓了一跳。
那小孩儿见她注意到了这边,拉开身旁的门,示意她进去。她举着弯刀,顺从地随了男孩儿。
男孩儿随她进去后,很快转身将门关上。
但好在她特地留意过,这扇门的门牌没有任何图案。
关门后这扇门里的黑暗渐渐隐退,一阵风沙迷了眼,再睁开,她看到了色彩明丽的青青草地,和有着彩色木顶的房屋。她正站在一个屋子的窗前,身侧是铺了蕾丝布的小桌,立在此处身体浊气仿佛都被洗净。
她很感谢那个男孩儿将自己带进来。
西凌微低头,握住身旁细细的手腕,对那个在阳光下皮肤泛着暖光的男孩儿微笑。
她喜欢这样一个并不光怪陆离的美好梦境。
男孩儿忙踮脚推开面前的窗户,让阳光更好地照在她身上。
她敛起袍子,坐在桌前望着窗外。像这样一个美好又安静的午后,她没什么要做的事,便撑着脸准备发呆。
这时房间角落里一个小女孩儿走了过来,说的内容并不客气,但里里外外都透着亲昵:“应忌玄,你又把她带过来。”
小男孩儿转身看着她,语气冷淡:“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能干扰她。”绝对的话语,陈述的语气,“你没有权利。”
事实被尖锐地讲出,应忌玄攥着双拳,看上去丝毫没有为这责难羞愧,可脸却在沉默里慢慢腾红。
西凌微听着两个小孩子的对话,心想或许她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只是不记得了。
他们两人间的战火渐渐烤出了糊味,看在下午这么美好的份上,她对着那个小女孩儿浅浅微笑:“你好,是我自愿跟他进来的。”
应忌玄肉眼可见松了口气,这让注意到这小动作的西凌微怀疑他刚才的紧张是在害怕自己也会责怪他。她托腮在桌沿,轻轻笑了。
应忌玄皱眉看向小女孩儿:“你可以走了。”
“她不会喜欢和你这样无趣的人讲话的。”女孩儿走过来,坐在了西凌微面前的凳子上,看着她头顶的斗篷和立在一旁的弯刀,不徐不缓直视她的双眼,“你起初是从一艘小船上下来的,对吗。”
西凌微为她双眼里不合年龄的洞察感到惊讶:“是,小船下面是长廊,里面一排排房间里是噩梦。”
“那就对了。”女孩儿移动眼球看了应忌玄一眼,再迅速收回,“他,总是仗着你对他的喜欢想要打破各个梦境的界限,把你拉回这个根本就不是你梦境的世界。”
西凌微没关注这告状,只缓缓道:“你是说……这是我的梦?”
“不是,这个绝对不是,可我只知道这个。”女孩似乎也说不清楚,就在她刮着下嘴唇思考时,应忌玄将那热乎乎的小手塞进西凌微垂一旁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