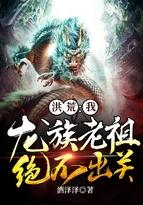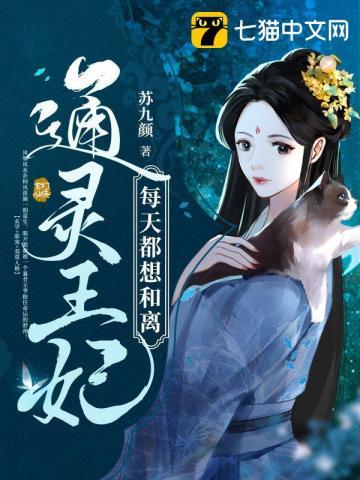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以下犯上百科 > 请君一(第1页)
请君一(第1页)
谢攸回到晋王府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
晚霞温柔地铺满天际,将流云染作浅浅的胭脂色,为亭台草木都披上一层暖意朦胧的薄纱。
他遣开宁昼,独自坐在李焉隅的药圃小亭中,终于得了片刻清净。暮光穿过枝叶缝隙,落在他的面具上,映出淡如初樱的晕。
四周弥漫着清苦微甘的药香,一丝一缕,静人心神。他慢慢将纷杂的心绪抚平,独坐良久,把这两日的际遇逐一细想。
周涣、李焉隅、容斟和、柳执因、谢檐礼。
这些人如走马灯般掠过眼前,留下若即若离的牵连与疑窦,又悄然隐入迷雾深处。
谢攸不知,究竟是谁执意要将他拖入这京城的暗涌之中。
但他明白,若非权势煊赫、翻云覆雨之手,绝无可能将这些人都推至他眼前。
李焉隅地位超然,容斟和亦非易与之辈。即便是周涣,想要精准地送到他眼前,亦是需要费些心思的。
而这些,都尚且留有余地。最令他心神难安的,是柳执因与谢檐礼。
前三人皆与书院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周涣家人牵涉其中,李焉隅是书院案的主审,容斟和则正在经办与之相关的另外两桩案子,将这三人拉扯在一起,缘由是很明显的。
可柳执因和谢檐礼呢?
他唇角牵起一丝极淡的苦笑。
这两人,虽与书院案无甚关联,却也并非毫无瓜葛。他们都与“谢攸”二字,缠着难以言说的宿缘。
这京城是不能再留了。那幕后之人既连谢檐礼与柳执因都能引入局中,怕是已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对方或许尚未拿到确凿实证,才未将他的身份公之于众,而是采用这样迂回的方式,将一切送到了他眼前。
然而,“那个人”如此悄无声息又大费周章地,将这些人一个个送至他面前,究竟想要看到什么呢?
谢攸凝神,细细忖度良久,觉得除却书院旧案,似乎再无其他可能。
思绪至此,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这桩十五年前的旧案。
自观心山上醒来时,他脑中一片混沌,唯一清晰的念头便是:我是书院案的凶手。
可如今仔细想想,动机、经过、细节,这些全都模糊不清。唯有这念头如烙印般刻在心底,像独立于浮萍之间的参天大树,着实诡异。
谢攸自认并非嗜杀之人。
他习医的初衷很纯粹。起初,不过是因为父亲总忽视他。那时他年纪尚小,心思也简单,只想,若能让父亲少些病痛,或许就能多得一丝垂怜,多让他爱护一点。
后来才懂得,母亲是父亲心中永难愈合的创口。父亲每见他一次,便想起母亲因生产而雪崩离世的那一日,无异于梦魇重现。
这才有了许多年的疏离。
幸而他于医道还颇有几分天资,又得拜在柳悯修门下,得他倾力教诲。他听老师讲述过许多未入太医院之前,悬壶济世的往事。
再后来,他自己也开始独立行医,尝过救人痊愈时的欣慰,也有过无力回天时的怅惘。
他便想,若能救治更多人,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