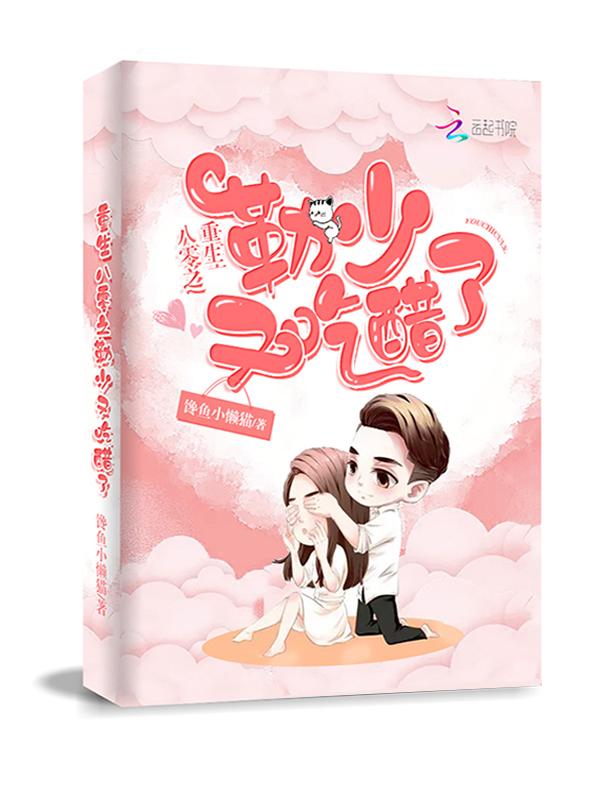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妖精报恩的电影 > 桃李春风一杯酒(第1页)
桃李春风一杯酒(第1页)
山匪一事就这样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落下帷幕,学子们议论纷纷,最终也没论出什么好歹。反倒是学院下了禁令,严禁任何人再讨论这件事,违者要罚跪圣人堂,才把这群少年人的奇思幻想全都压下去了。
又过了不些日子,这件事就如同嚼尽汁水的甘蔗渣,随意地被众人抛诸脑后,还不如“某某学子顶撞夫子被逐出学院”“某某师兄与花楼头牌的爱恨情仇”来得有趣儿。
至于吴漾,虽然不时会莫名不安,但毕竟同好友们吃住一起,平时课业又忙,总之也再不提这事了。就算偶尔想起,也强迫自己尽快忘掉,或是做点别的什么事转移注意力。
最要紧的是,这些日子他真的不再倒霉了!也许真的是像徐文正说得那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吴漾很快又过上了晚上蒙着被子看小说,白天课上不断打瞌睡的日子。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等吴漾吃腻了樱桃,馋上了冰梅汤,转眼已是盛夏时节。待到五月又逢五,这一年的端午节也如约而至。
本朝有令,除元旦、元宵和冬至以外一律无节假,不过民间庆贺的氛围依然浓厚,家家门插艾叶,处处户挂灵符。县学虽然也不放假,但解了晚上的门禁,也让这群小子有家的回家,有野的撒野。
吴家虽世居江宁,但吴漾父亲调任应天府,母亲也随夫上任,家中空荡荡的,也没有回去的必要。
不少官家子弟也同样如此,便商量着找个画舫一同夜游作乐。
吴漾不想去,觉着还是早早洗漱完,配着果酿粽子、窝在被窝看画本小说舒坦。谁知徐文正听了连忙把家宴推了,求到吴漾跟前:
“好哥哥,我求你了!你就去吧!我爹听说我是和你出来的才放人的!你忍心看我今晚上被‘强抢民男’吗?”
吴漾“扑哧”一声笑出来,伸手点徐文正额头:“色胚子,不去做翻墙的登徒就算好了,还担心别人强了你?还不如担心担心天会不会塌下来砸你身上呢!”
民间早婚,徐文正家里早就想给他娶一房妻子,最好能马上让徐家父母过上含饴弄孙的日子。
徐文正苦着脸:“我自己的亲事自己又做不了主,有什么意思?况且我还年轻,我还有许多事要去做,才不要早早定下来。”
吴漾叹道:“这种事,又有几个能由得自己呢?”
既然徐文正都开口求他了,吴漾自然也只能应约前往。汤衡有家宴不提,张景载本来就要参加夜游,一听徐文正和吴漾来更为高兴,当即拍拍胸脯包了这桩事,只让两人好好坐着等,他安排好了派人来接。
等到余晖散尽,二人趁着昏暗的天色出了门,正欲上马车,却听一道男声冷不丁响起:
“我也要去。”
吴漾闻声猛地回头,却见华灯初上,淡淡暖光照出风清月朗的少年。
“瑞……珩瑞?!”吴漾有些难以置信。
徐文正倒吸一口冷气,眼前这个面瘫脸竟是赫赫有名的李珩瑞!
县学分六堂三级,以学生的程度和年龄划分递升,徐文正和吴漾所处的“修心堂”属中级,李珩瑞所在的“率性堂”则是最高级,说起来还要称他一声师兄。
而李珩瑞本人的出名不在出众的容貌才学,而是他的木讷迂腐:老古板的班头,书呆子的领袖!同他搭话十次能碰十鼻子灰,十年如一日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这也就算了,关键这厮还十分地不近人情。虽然人缘不好,但夫子们全把他当个宝,看他的眼神慈祥如看自家子侄,恨不得将此兰芝玉树挪栽到自家门前,因此李珩瑞经常被委以助学的任务。而面对他的一众同窗们——
网开一面?不存在的!一切违规皆记!录!在!案!
为此,不少人都对李珩瑞这个“鹰犬走狗”颇有微词,不是没有人看不惯他,但这厮根本视你如空气!活活一拳打木头上,又气又疼,偏偏人家还不当回事。
眼下这尊大神主动要跟他们一起去游船?这画面太美,徐文正别说看了,想都不敢想。
吴漾嘴角抽搐:“李师……呃,你不是最不爱凑这种热闹吗?不必勉强自己,别去了吧。”
徐文正内心疯狂点头,是啊是啊,您老要去了大伙还能玩得起来吗?还是不要为难自己、刁难他人了吧!
李珩瑞面无表情地看向吴漾,缓慢而坚定:“我不,我就要去。”
吴漾:……行吧
“这就是你们把这大佛带过来的理由?!”张景载抓狂,把吴漾和徐文正拽到一边低声耳语。而那边李珩瑞悠悠进了船舱,原本热闹喧嚣的舱内瞬间安静,立竿见影。
“他非得跟过来,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给他踹下车吧!”吴漾嘟囔道。
“天呐!他又打的哪门子主意!山长派过来的耳报神吗?”张景载眼前一黑。
“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吴漾立即辩驳张景载,声音都不自觉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