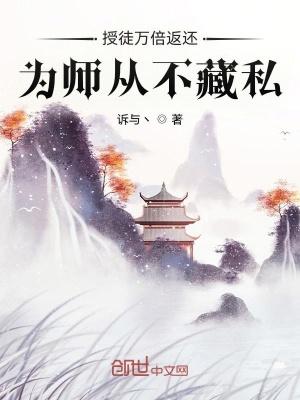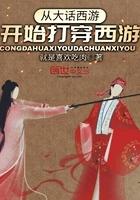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逢的路 > 第 2 章(第3页)
第 2 章(第3页)
池烨没敢再多看一眼,盯着前方的远山:“雨停了去哪儿?”
“师兄去哪儿?”周予骎慢条斯理地擦去身上的潮湿,顺手把沾湿的皮质座椅也一块儿擦了。
“毕节。”
“巧了,我也去。”周予骎笑,眼睛弯成月牙,映着车窗外的光。
池烨皱眉看他,满心狐疑,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妈是毕节人啊。”周予骎把用过的纸巾塞进车里的垃圾袋,“算了,反正师兄肯定已经忘了我说过的话。”他耸耸肩。
“哦。”池烨低低地应了一声,声音闷在喉咙里。原来只是回家。
车窗外的风景在雨后的水汽里模糊,他觉得自己刚才那点隐秘的、几乎是自作多情的揣测,像被戳破的气泡,无声地炸开,只留下一点尴尬的、黏手的湿意,粘在指尖,挥之不去。
他几乎是有些仓促地另起了话头:“暑假回家?”
“我已经毕业了,师兄。”周予骎看着他。
“这么快?”池烨脱口而出,是真的有些意外。时间的流逝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撞了他一下。
“去英国水了一年,毕业很快的。”
确实太快了。
池烨的目光落在窗外湿漉漉的绿色山峦上。脑子里闪回的最后画面,是他自己研三毕业典礼上喧嚣的烈日,穿着硕士服的身影在热浪里晃动,人群里那个笑容灿烂、带着点少年气的大二师弟周予骎,仿佛就在昨天。一转眼,对方竟也研究生毕业了。
但这三年对池烨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日复一日,连空气都像是凝滞的,循环往复,没有留下多少鲜明的印记。
入了社会,生命好像被偷走了流动感,日子死水一般,连时间往前走的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窗外的风裹挟着黔地山林特有的、湿润清冽的草木气息涌了进来,带着一种无声的提醒,关于时光的流逝,以及某种他自己尚未厘清的东西。
“那你工作怎么样?”池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好奇妙。
这是池烨第一次同周予骎聊工作,印象里他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那时候他们总是聊不痛不痒的日常。
“出国前和朋友开了几家民宿和咖啡店,这两年贵州文旅做得还不错,游客蛮多的。”周予骎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有些许不同,“小时候总想着往外跑,但是长大了觉得能回来建设家乡也不错。”他故意隐去了一些细节,比如创业的钱从何而来,为什么出国之前做这些,和谁一起经营。
“阿姨是毕节人,少数民族?”其实池烨压根没在意他的情况,随意地岔开话题。
“嗯,彝族。”
“毕节好像彝族更多些?”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吧,师兄感兴趣?”
“现在自己随便写点东西,想多了解一点民族文化。”
“那你可以在毕节逛逛,乌蒙山,奢香夫人纪念馆,还有些彝寨,你都可以看看,现在天气也合适。”
“那太好了,真来对地方了。我本就是来避暑的,顺便采采风。”池烨说着,“离职有一段时间了,明明自己也不怎么喜欢法律,但离开它,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你之前好像挺爱上班的,像工作狂。”周予骎记得他总是很忙,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吗?”池烨很震撼自己居然给了别人这种错觉,“那看来我以前还是太装了。”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
池烨一手撑在方向盘上,一手扶额,一边笑一边摇头。
周予骎靠在副驾椅背,右手手肘支在窗沿,手搭在太阳穴,头微侧,目光稳稳地落在池烨身上,像收藏多年的旧信终于重见天日,要逐字逐句摩挲。
水珠顺着玻璃窗蜿蜒,轻敲窗框的声响,和心跳声缠在一起,成了此刻最隐秘的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