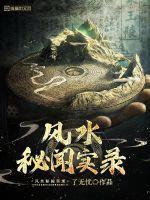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我成了我的二大爷 > 尘埃落定协议成婚(第3页)
尘埃落定协议成婚(第3页)
条款冰冷、直接、不留情面,充满了商人式的利益切割和风险规避。尤其是那“十倍偿还”的条款,如同一座沉甸甸的大山。
两千元,在1988年,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而两万元,更是天文数字。
萧阅的目光在“贰万元整”那几个字上停留了两秒,指尖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再看第二遍,伸手拿起了书桌上准备好的一支黑色钢笔。
笔尖悬停在签名处。
楼时靠在宽大的椅背里,双手交叉置于腹部,冷眼旁观着。他看着少年拿起笔,看着他那双过于沉静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退缩,看着他落笔——
萧阅
两个字,力透纸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签完名,萧阅放下笔,将协议推回楼时面前。
楼时拿起协议,目光扫过那签名,眼神深处似乎有极细微的波动,快得难以捕捉。他也拿起笔,在另一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楼时。
两个字,笔锋凌厉,如同刀刻。
一式两份。
楼时将其中一份递给萧阅,另一份收进抽屉。然后,他从书桌一侧拿起两样东西,放在了萧阅面前。
一把黄铜色的、带着磨损痕迹的老式钥匙。
一沓用牛皮筋整齐捆扎好的钞票。
崭新的、墨绿色的十元面额纸币,正面印着工农兵和人民大会堂图案,是1988年正在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厚厚一沓,整整两百张,两千元。在这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这笔现金散发着一种沉甸甸的、令人眩晕的诱惑力。
“西郊槐树胡同14号。”楼时言简意赅地报出地址,声音依旧没什么温度,“钱,点清楚。”
萧阅伸出手,指尖先触碰到那把冰凉的黄铜钥匙,金属的质感让他心头微微一颤。然后,他拿起了那沓沉甸甸的钞票。纸币特有的油墨味和新纸的脆响传入鼻息。他没有像没见过世面的人那样迫不及待地清点,只是用手指捻了捻厚度,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份量,便将其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旧挎包内层。
“清楚了。”他抬起头,看向楼时,眼神平静,“谢谢。”
这句“谢谢”,无关感情,只是契约达成的确认。
楼时没有回应这句感谢,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复杂难辨,最终归于一片沉寂的深海。
“老陈会送你过去。”他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不起眼的按钮。
很快,那个带萧阅进来的冷峻年轻人(老陈)出现在门口。
“送他去槐树胡同。”楼时吩咐道,语气不容置疑。
“是,时哥。”老陈应声,对萧阅做了个请的手势。
萧阅最后看了一眼书桌后那个沉默如山岳的男人,拿起自己的旧挎包,转身,跟着老陈离开了这间决定了他重生后命运走向的书房。
---
槐树胡同14号,是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
院墙不高,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推开有些斑驳的黑色木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青砖铺地,墙角有一口盖着石板的老井。正房三间,青砖黛瓦,门窗是旧式的木格棂,糊着白纸,显得有些古旧,但整体收拾得干净利落,比萧阅那个破败的家强了不知多少倍。
老陈将萧阅送到门口,把钥匙交给他,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转身便蹬着自行车离开了。
萧阅独自一人站在小院中央。
夏日的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环顾着这个陌生的、即将成为他新起点的“家”,心中五味杂陈。
没有欣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两千元的债务,三年的期限,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走到正房门前,用那把黄铜钥匙打开了门锁。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
屋内陈设简单,但一应俱全。
老式的木床、桌椅、衣柜,虽然陈旧,却擦拭得很干净。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灰尘和阳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