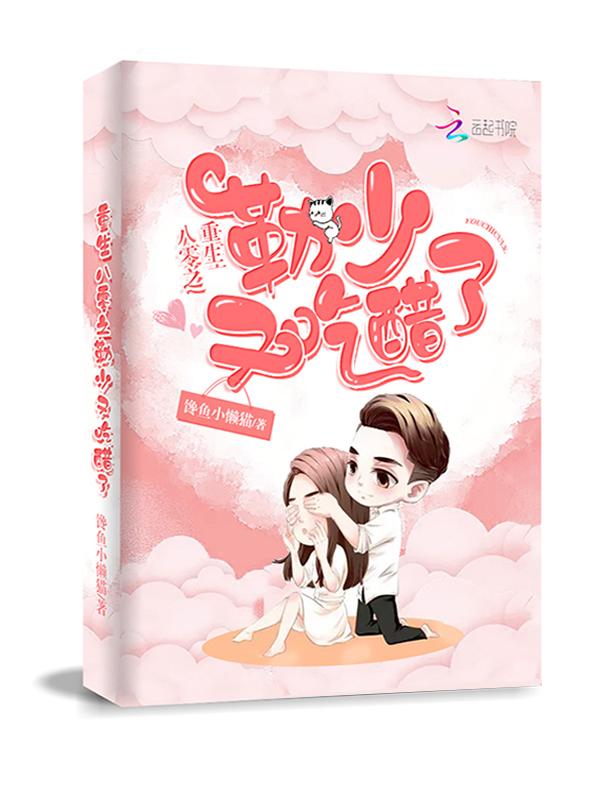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逐臣的拼音 > 婚约(第2页)
婚约(第2页)
阮阮远远向他招手,一群小丫头们见是文砚,便叽叽喳喳簇拥上去。阮阮把油纸包塞到闻礼之怀里,“好哥哥,你可算来了。这是厨娘多塞给我的酥糖,我刚给姐妹们分了一圈。你再来完些,可是渣都不剩啦。”说着,点了点旁边春桃丫头的鼻子。春桃假作嗔怒,笑着嬉闹回去。
“别挤别挤——哎哟!”马夫老赵故意板着脸,手里却稳稳扶着差点摔倒的小丫鬟。几个姑娘挤在廊柱旁,你推我搡地笑作一团。
“文砚哥前日教我的‘福’字,雅兰姐姐都说写得端正!”春桃得意地扬起下巴,指尖在空中比划,“先一横,再一竖……”
“就你这字,写得像鸡爪子。要我说,你雅兰姐那是哄着你——”老赵插嘴,春桃闹着要锤他,被阮阮拦下。
“听说你会仿人字迹?”厨娘挤挤眼,“能学学世子的字儿不?”
闻礼之接过阿德递来的纸笔,笔尖一顿,忽然在纸上写了个“滚”字,连笔的嚣张劲儿活脱脱是时琛手笔。众人哄笑,阮阮笑得险些打翻闻礼之手里的酥糖。
“文砚这般俊俏,定是定了亲的!”雅兰红着脸打趣。
“没有。”闻礼之截住话头,耳尖却红了。
丫头们不肯放过他,闻礼之笑着摇头:“幼时确有一门婚约,只是……”
“——只是什么?”
笑声戛然而止。
时琛拎着马鞭立在月洞门下,红绸发带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院内众人齐齐跪下。时琛缓步走近,鞭梢挑起闻礼之下巴,“婚约?我倒不知,奴隶也配谈婚论嫁?”
“幼时玩笑,世子……”闻礼之话音未落,鞭风已撕破他衣领。
“侯府禁止奴籍私通!”时琛一脚踹翻水桶,泥水泼了众人满身。他鞭梢卷住闻礼之脖颈,“我看你文砚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阮阮欲上前为闻礼之辩解,被雅兰死死摁住。
时琛不轻不重地瞥了一眼侍女的动静。
“既然都这么闲——”他突然反手抽碎石凳上的茶盏,“那就全去庭前跪着!跪到想起自己身份为止!”
众人战栗退下时,闻礼之却被一双手勾住衣领。时琛贴着他耳畔轻语:“你刚才说……‘只是’什么?”
温热吐息拂过颈侧,闻礼之却脊背生寒。
沉水香烧到第三轮,香灰在青瓷盏里积了厚厚一层。闻礼之被拽着踉踉跄跄拖过三道门槛,腕上镣铐的印记又覆上擦伤的红。
时琛在愤怒。
他在愤怒什么?
闻礼之敏锐地察觉到,时琛今日的暴戾里混着别的什么——像是……焦躁?
这个念头刚起,后背就重重撞上博古架。一只霁蓝釉梅瓶摇晃着坠落,被时琛抬脚接住,又狠狠踢到墙角——“哗啦”一声,碎瓷像雪粒子溅到闻礼之脸上。
时琛的呼吸很重。
不是那种跑马后的急促。十八岁少年鲜活的气息扑在颈侧,像猛兽狩猎到猎物后,血液沸腾,瞳孔放大,心脏被名为亢奋的情绪填满时那种又轻又重的喘。闻礼之太熟悉这种征兆了——每每时琛与侯爷议事不顺,回来总要摔些什么,自己也要被多加刁难。
但今天不太一样。
那双手死死掐住他后颈时,闻礼之看见时琛眼底有东西在烧。不是往日那种玩味的火,倒像……流放路上的湿柴,噼里啪啦地爆燃,只是怎么也捂不暖身体。
“一个奴隶。”时琛的拇指碾过他下唇,蹭掉那点酥糖留下的糖渍,“也配提婚约?”
铜镜很凉。
闻礼之被反拧着胳膊按上去,铜镜的腥锈气涌进鼻腔。他急促的喘息在镜面呵出白雾,又很快被时琛压上来的体温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