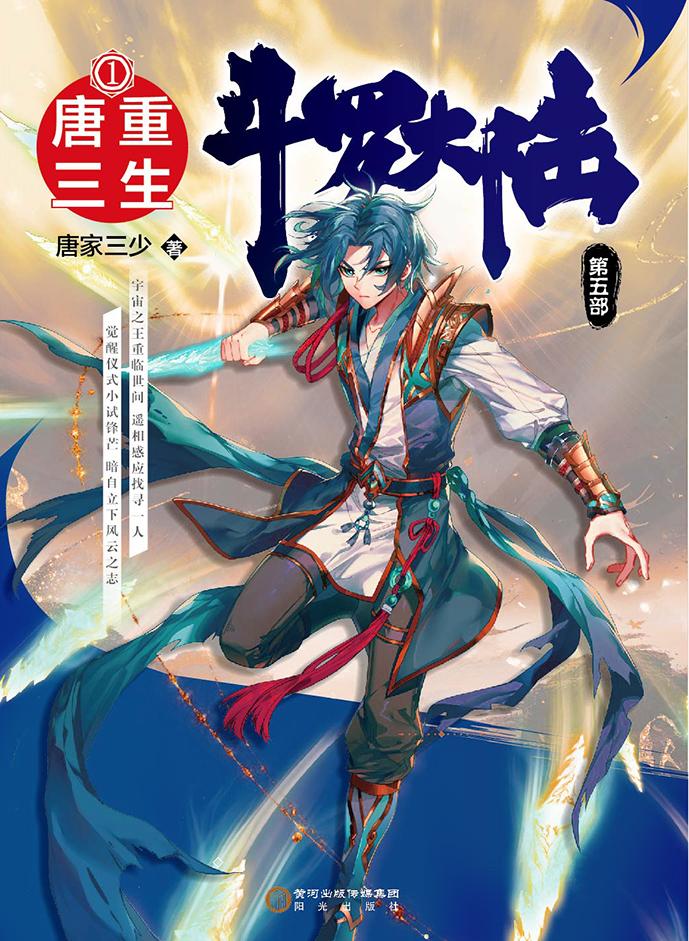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朋友阔绝 > 山雨(第2页)
山雨(第2页)
“父亲召我何事——”
话音戛然而止。
裴霄雪正用麈尾拨弄着博古架上的青瓷瓶,闻声回头,白玉柄映得他眉眼如刀:“世子来了。”
时琛后颈寒毛倒竖。
闻礼之立在廊柱阴影里,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在他的肩头,浸透了单薄的衣衫。
没一会儿,裴霄雪便踏出厅门。雨幕如织,那道白衣身影在廊下划过一道冷光。
闻礼之心头一骇。
尚且还未来得及平复呼吸,那道身影却突然驻足——
雨帘中,锐利的目光破空而来。
闻礼之的呼吸骤然停滞。
被洞穿的战栗感瞬间攫住咽喉,窒息般的压迫感榨干了肺里的空气。
他知道我在这——
裴霄雪眼中映出的,分明是永州官道上囚车里那个戴枷的少年。雨水顺着额发滚落,与冷汗混作一处,在衣襟上洇出深色的痕迹。指尖的温度被尽数抽离,心跳声震耳欲聋。
裴霄雪并未久留。
一个眼神便已足够。
白衣没入雨雾的刹那,会客厅内骤然爆发出瓷器碎裂的锐响。少年压抑的怒吼与低沉的呵斥穿透雨幕,连窗棂都在声浪中震颤。
闻礼之垂眸。
睫毛承不住的水珠簌簌坠落,在锁骨处积成冰冷的洼。
霎时,一个危险的想法涌上心头。
急促的吐息在冷雨中凝成白雾,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软肉。喉结剧烈滚动的声音竟比渐近的雷鸣更为清晰,心脏剧烈跳动,几乎要撞碎肋骨。
——此举,若堕深渊,则万劫不复。
思绪在颅内似沸水般翻滚,他突然狠狠一闭眼——
”吱呀——”
书房门在闪电亮起的瞬间,悄然洞开。
闻礼之的指尖突然痉挛,文书被捏出几道皱痕。他盯着自己失控的手指怔了一瞬,随即用沾满冷汗的掌心压平纸页。
他强迫自己深呼吸,每一次翻页都小心翼翼,确保不移动纸张原本的位置。案几上堆着寻常的户部文书:蓟镇军饷的批红、江南治水的奏报、盐税清册——侯爷掌财权,这些都不足为奇。
不对。
他猛地拉开抽屉,里头整齐码着更多公文。闻礼之随手抽出一卷,竟是十年前谢闰章出使北狄的旧档,边缘还沾着干涸的茶渍。再翻,是近月的边关急报,朱批字迹凌厉如刀。
越看,思绪越乱。这些零散的文书像被刻意拼凑的残局,隐约指向某个骇人的阴谋,却始终差最后一子——
直到他的手指碰到一张对折的名单。
展开的刹那,血液骤然冻结。
朱砂圈出的十几个名字,全是谢闰章的门生故吏:监察御史刘淼、刑部主事林守谦、蓟镇参军赵朔……这些人如今或居要职,或戍边关,却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全是清流中竖。
太阳穴突突狂跳,碎片的线索在脑中翻涌:北狄文书、军报篡改、这份名单……
还差最后一块拼图。只差最后一点,就能拼出全貌——
“砰!”
门板撞在墙上的巨响炸在耳边。
腕骨上传来的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
慌乱的视线撞进时琛那双赤红的眼睛——那里翻涌着太多情绪。震惊、愤怒、背叛,还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