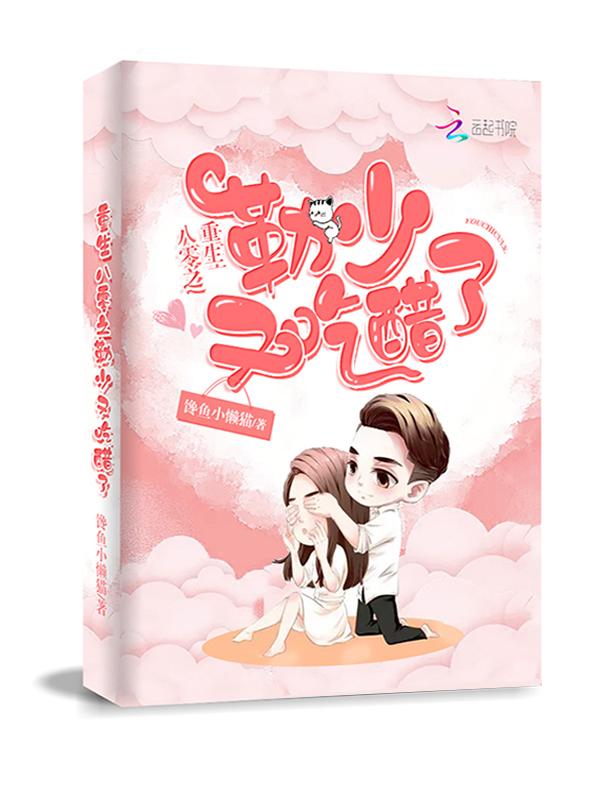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摇滚学校歌曲 if only you will listen > 第82章 082 无冕之王(第2页)
第82章 082 无冕之王(第2页)
卫真烦躁得不行:“给我关上!”
傅莲时终于带上门。他靠在门板上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换歌吧,唱《火车》。”
“为什么?”高云说,“要是唱《火车》,会不会被商骏偷走?”
“偷走就偷走吧,”傅莲时贴着门缝听,“一首歌没有了,反正可以再写。你们难道不想赢吗?”
众人不敢作声,傅莲时把门重新打开,让龙天的歌声无遮无拦地传进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傅莲时说:“曲君哥,要是唱《火车》能不能赢?”
曲君说:“可以。《火车》,只要听两句,大家都会喜欢它的。”
“那你答不答应唱它?”傅莲时问道。
曲君道:“为什么问我?这是你写的歌。”傅莲时赧然说:“因为是送给你的。”
曲君笑道:“我没有意见。”
傅莲时转过身,看着东风乐队。
按原来的选曲,他们只需要贺雪朝一把吉他。但演《火车》就得多一道节奏吉他的音轨。卫真拿出自己的琴,坐下调音,意思是同意了。贺雪朝和高云当然没有意见。
不过灯光来不及协调了,只好用基础简单的模式。
龙天唱完了,管弦乐团七手八脚撤下。工作人员忙着搬凳子,搬大件,没人搭理东风。东风一行人只得摸黑走上台阶,自己理好连接线。
甚至没人发觉东风已经上台。卫真在暗中道:“今天唱一首新歌,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唱过的,叫《火车》。”
不等观众欢呼,沉郁的贝斯响了数下,接着是紧密、轻盈、薄薄一片的吊镲,月亮一样越升越高,笼罩整间体育馆。
东风请不起交响乐团,但摇滚乐队自有一套丰富听感的方式。譬如说,鼓慢是温情,快是热烈,对称是理性和沉稳,不对称是风趣和机变。吉他的音色永远是吉他,加入频繁的推弦、颤音,旋律是呜咽、冷冽的;加入连续的滑音,乐句就好像行船,有了阻滞也有了决心。
《火车》是东风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首歌,从头至尾九分半钟,光前奏要弹三分钟,胜过别人大半首歌。
很难在《火车》找到别的乐队的影子。总的来说是一首快歌,一箭离弦那样畅快而果敢,但在大开大阖同时,编曲却极尽细腻节俭。无论吉他、贝斯、鼓,珍而重之在每个乐段、每个乐句,花枝招展地炫耀技巧。技巧之间精心安排过,绝不会显得太滥、太腻,好像看见一树玉兰花,多即是繁荣、繁华,只希望它越开越多,没有希望它凋败的道理。这首歌明摆着告诉一切听众,东风能弹一切的音乐,能克服世上一切的阻碍。
弹了两分多钟,观众一直看不清东风的面容,只隐约看见四个轮廓,被丝线般细细的白色光照勾勒出来。深藏在黑暗之中的激情。终于交响乐团撤完了,台上突然光芒大盛。卫真靠近立麦,终于唱出第一、二句歌词。
听清之后,场馆反而安静了一瞬,旋即爆发出更为激烈的尖叫。跟曲君说的一样,只要听上一两句,大家都会喜欢《火车》。
为给器乐让出空间,《火车》的副歌动听简单,有大量重复乐句。即便是一首新歌,唱到中间部分,歌迷也都学会唱了。三千人的体育场,有三千人在合唱,假如这首歌能够传扬得更远,在五千人的场馆,则会有五千人合唱;在红磡、在东京巨蛋,能有一万或五万人合唱。如果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会有五十万人合唱。
器乐在行进,一浪又一浪,将气氛托升得愈来愈高。高云的鼓开始变速,越敲越快,贝斯、吉他,重复着相同的尾奏,也愈来愈快愈来愈快,像轰鸣的火车,像飞机像火箭。三千人的小世界,被这无与伦比的速度充盈了。吉他的啸叫声、密密麻麻的鼓点,渐渐不分彼此,融合成整片迷幻的音墙。只有贝斯像车轮,仍然冷静、自若,条理分明地前进。
卫真脱下背带,把琴高高地举起来。他今天弹的是一把吉普森“夜鹰”,其实等于娇小、异形版本的“LesPaul”,钢琴黑色。
绕场走了一圈,卫真双手擎着琴颈,往地上狠狠砸落。
一曲终了,乐迷不知疲倦地叫着:“东风!东风!”张贾刻意等了两分钟,然而东风的呼声不减反增。再不颁奖恐怕来不及了,张贾硬着头皮,请评委宣布结果。
佚名声嘶力竭说:“今天所有的演出,已经结束了!评委认为有一支乐队达到了国际水准!”
大家说:“东风!东风!”佚名说:“我宣布……”
大家又说:“东风!东风!”
佚名道:“……‘第一届北京摇滚歌手比赛’的冠军是……”
淹没在狂风骤雨般“东风”的呼声之中。吃剩的包装袋、喝空的矿泉水瓶,连珠丢下来。张贾道:“安静!都安静!”歌迷越叫越大声,拍手跺脚,好像不需要喝水休息,嗓子不会破,能无休止地叫下去。
张贾朝中控做个手势,霎时间灯光全部转暗,场馆陷入混乱之中。卫真一愣,喝道:“张贾,操你丫的,出事故了你能负责吗!”拿话筒说:“都别站起来!坐下,都坐下!”
傅莲时眼疾手快,死死掐住张贾的手臂。张贾使劲掰他的手。就要掰脱了,傅莲时叫道:“高云哥快来!”
高云道:“你的灰指甲还会发光。”把张贾拿住了。
张贾走不脱,只好说:“快开灯!”中控又将灯光打开,评委席已趁乱走得空了。
人群一阵欢呼,继续叫:“东风!东风!”张贾被押在台上,拼命大叫:“快让他们停下来!”
卫真拍了拍话筒,右手往下压了压,人群果真安静了。张贾长舒一口气,卫真对着那话筒道:“我们要见商骏文化的老板,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