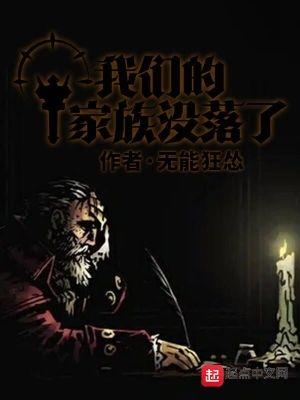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不是你白月光 > 19第十九章(第6页)
19第十九章(第6页)
哪怕是阿父,也是大母生下来的,而大母也是女子。
林榆拗不过她,笑说:“好好好,女先于男。兄长心里,阿鸢永远先于任何人。”
她如今长大了,不再胡搅蛮缠。
她缓缓思量道:“男子不一定刚,也有柔弱之处,女子不一定柔,会有刚强之时,女子也可以是君子。再说了,刚不一定胜于柔。所以,男子也并非先于女子。”
她忘了看萧珣的脸色。
待这些话说完之后,她也不敢看了。
心如擂鼓,在胸腔里咚咚地敲出闷响,她在沉寂下来的殿中,恍惚听见了……钟声。
不啊,是秋蝉的悲鸣,落叶的簌簌声。
那些声音里夹了森然的笑,像是天上而来,又像是灵魂出窍的自嘲:“你真敢说啊。”
“不敢,再不敢了。”她悻悻,喃喃自语。
身子因那笑里的寒意,结了冰,僵了。
“是我先问的。想怎么答就怎么答。”是萧珣的声音,“何况,你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
林鸢确信这声音不是来自地府,也不是来自天庭,才回过了魂。
萧珣似乎并无愠色。
“刚与柔,不应以男女而分。古来要强的女子不少,娥皇女英,妇好,太姜太姒,周宣姜后,无盐之女。”
笑也传了过来,“还有,你。”
林鸢的脸,被这话,还有说话人落在耳边上的,酥酥麻麻的气息,灼得通红。
“姊姊的脸为何红了?”阿瑶的声音也落入了她的耳畔。
“风吹的。”林鸢闷声道,将兜着头套着的羊羔裘又拉得紧了些,只剩了一双眼。
翠微山还是冷,不过,雪已经停了多时,风也小了。
她看到鹅毛大的雪片,在半空一闪而过。
“呀,又下雪了么?”
等阿瑶抬头看去,却什么都看不到了。
“姊姊看花了眼吧。大概是大家口里边吹出来的热气。”
阿瑶偏着头,在呼出来的白气里,远远瞧见了玉树临风的世子。
一支羽箭在萧锦的眼前掠过。
箭镞擦过铜锅的一耳,稳稳落在了三尺口径的锅中。
细小的碰撞声几乎不可察觉。
萧锦回过神,惊出了一身汗,来不及唤吏卒,一手握紧了身上的秦王剑,一手发着颤,将那支羽箭取了出来。
鎏金的箭镞。
上面的印花,他认得。
是羽林骑的箭矢。
他向方才那支箭飞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些围坐着的人群之外,停了两驾陌生的马车。
灰色的帷帐,不饰纹绣,低调非常,看不出来自哪一个世家。
驾车的马却齐齐一色,都是毛色如缎。是大宛的马。
一个腰束玉带的皂衣男子微微低着头,躬身侧立,手上执着箭囊。
车帘拉开了一半。
满绣的袖口在风中轻曳,扬起的时候,能看见一支金箭搭在挽成了满月的雕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