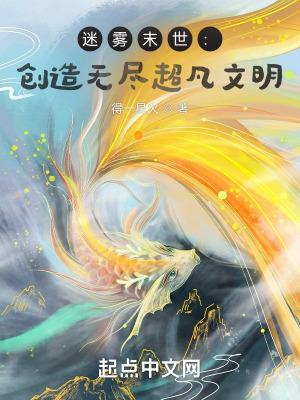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下等仙师免费阅读 > 8090(第16页)
8090(第16页)
李恕又问管事:“既然如此你今天又来这里做什么,是不是想毁灭什么证据?”
“没有,绝对没有!”管事大呼冤枉,然后小声嘀咕,“我是觉得我们庄主可能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所以才想来这里驱驱邪。”
李恕要他说清楚些,管事叹了口气:“方才我不是说过这个庄子就是为了给我们庄主养病才建的么,但我觉得最近庄主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管事跟了庄主多年,两人既是主仆也是亲人,庄主把试炼大会期间的事宜都交给了管事,所以他的事情骤然多了起来,但是只要有空他就会去看望庄主。
“你们庄主是何病症,需要安排那么多护卫守着院子?”
“不是啊,那些护卫是白羽观安排的,我们庄主的病也是他们治的。”
李恕心神一动,忽地想起那天夜里碰见的斗篷人。此前她一直想从沉璧身上找证据,即便得知那晚沉璧和有缺一起进了乱葬岗,她也还是没有打消疑心,如今看来,她可能真的先入为主了。
“关于你们庄主的病,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我们庄主的病是年轻时留下的旧疾,找了许多大夫都说没法根治,只能好好养着,说白了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白羽观掌门却说他能治好。吃了他的药后庄主确实有了变化,从前走路都要人搀扶,现在居然能健步如飞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更严重了?”
“这是因为庄主虽然身体好了,但是精神差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去十次他有八次都在昏睡,嘴里说着奇怪的话。我一开始以为是梦话,后来发现他每次说的都是同一句,好像是什么……弃凡胎,得长生?”
管事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在寻求长生不老,可是庄主以前病归病,心态其实比他豁达多了,即便被病痛折磨多年也没有自怨自艾,怎么会突然在梦里念叨起长生不老?
李恕和任流白对视一眼,这已经是她从第三个人口中听见这句话了,而且这三个人都和白羽观有脱不开的关系。
管事把能说的都说了,再次向李恕发誓:“小人老实本分大半辈子,绝对没有害过一个人,你可一定要跟那个鬼、鬼公子说清楚,别让他找错了凶手报错了仇啊!”
李恕抬手起势,管事背心一凉,浑身汗毛登时竖了起来,只听李恕说道:“我在你身上下了诅咒,若你真的心中不虚,明日戌时便在庄主院外候着,幕后主使是谁自会水落石出,在此之前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想必你也清楚。”
管事听见诅咒二字头皮发麻,结结巴巴道:“我我我知道,那那那这诅咒能解吗?”
“当然,我要找的是真凶,不是替死鬼。好了,你可以走了。”
管事得了敕令,强行把心咽进肚子里,手脚发软地站起身,自始至终没敢回头看一眼:“好,小人明天一定准时出现。告、告辞。”
待他走后,任流白蹙眉道:“白羽观的事情似乎不简单,就连管事自己也不甚清楚,他能出面指认吗?”
“不要紧,他只要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就行了。”
“你想怎么做?”
“自然是和白羽观当面对峙。”
任流白稍微一想,松开眉头。既然李恕这么说,那她肯定已经有了对策,自己只需要配合即可。
方才管事来得突然,他只来得及匆匆穿上衣服,一身痕迹都没清理,连珍珠也没取出来,这会儿没事了,任流白才意识到他的样子有多不成体统,忍不住扯了一下李恕的袖子。
“怎么了?”
“珍珠。”
李恕心里了然,嘴上明知故问:“珍珠怎么了?”
任流白难以启齿,把李恕的手贴上他的小腹,声音愈发微不可闻:“还在里面。”
“我知道呀,我说过送给你了,现在你可以把它带回去了。”李恕顺手揉揉他的腰,满脸写着真诚,“这是我特意为你选的,和你很相配,仙师一定会好好保存的吧。”
明白了李恕的意思,任流白浑身发软,体内好像又有水波荡漾。
“……我会的。”
从这里回玄隐门要穿过半个山庄,任流白走在路上,每一步都胆战心惊,他能清楚地感受到珍珠的位置,知道不会被外人看见,但他还是忍不住脊背紧绷,不敢有一丝松懈,任何人从他身边经过都能让他呼吸凝滞。
这种紧张的情绪在回到玄隐门时达到了顶峰,守夜弟子一见他就主动和他打招呼:“大师兄,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任流白点点头,根本不敢开口,他怕自己一张嘴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好在另一名弟子知道情况,替他解释:“大师兄在找证据证明应师兄的清白啊,反正我不相信应师兄会伤人。”
“哦对,我一下子没想起来。我也不信,我看是紫竹峰嫉妒应师兄还差不多,那大师兄你有找到什么证据吗?”
任流白站在院子门口,耳根悄悄烧了起来,体内水液越积越多,浸着珍珠,令他隐隐生出满胀之感。他不想撒谎骗人,又怕守夜弟子继续和他说话,一时进退两难。
“别问了,你没看见大师兄很累吗?”守夜弟子捅了同伴一胳膊肘子,示意他看任流白发红的眼尾,关切道,“大师兄辛苦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谢谢。”任流白尽力挺直脊背,减小步幅走进院子,此时此刻他竟庆幸珍珠还在,否则那些水液没了阻拦,还不知会流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