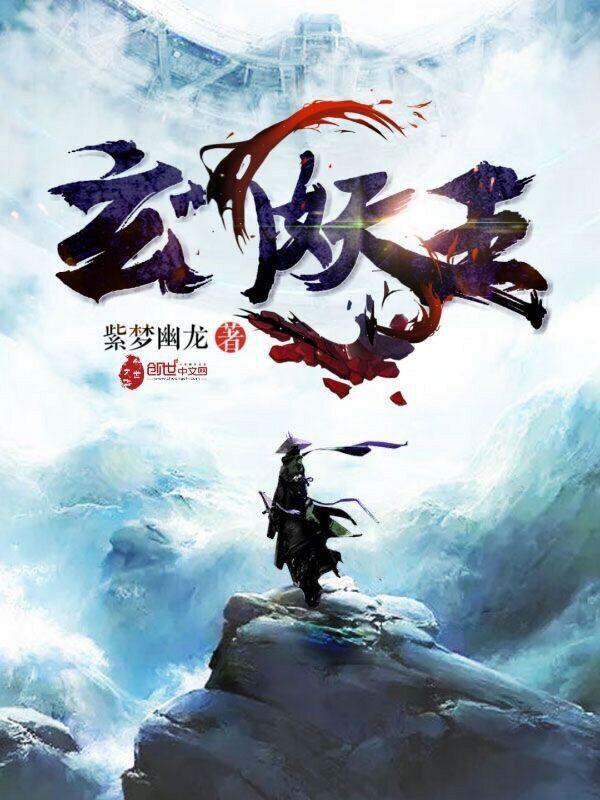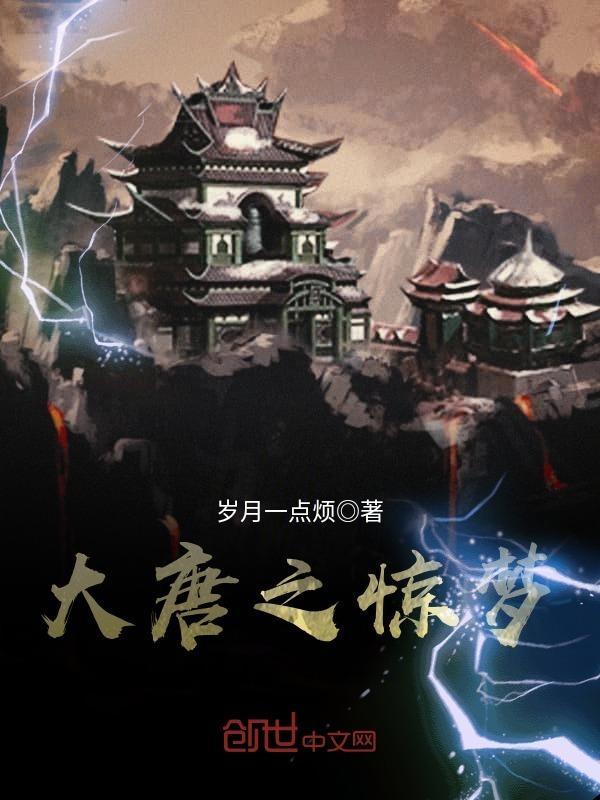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如此星辰如此夜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1929年,承倬甫经于伯焘引荐,进入了新成立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在南京任职了半年,做得不错,用于伯焘的话讲,“六爷一向洋派,搞风花雪月的事情比我们这些土包子强”。于是被调往上海,他的二姐夫随之就来上海开出一家“华夏水仙花电影公司”。不过他那个二姐夫死性不改,开电影公司还是为了玩女电影明星。没多久,承倬甫的二姐就忍无可忍,要跟他离婚,闹得沸沸扬扬,报纸上都是。这么一闹,外界就要求查承倬甫是否滥用职权,大搞裙带关系,有中饱私囊之嫌。
大概是作为此事的回应,次年年初,当离婚案闹上法庭的时候,承倬甫亲自写了一篇声明登报,澄清他与“华夏水仙花电影公司”没有关系,支持他姐姐离婚。但是他当年在北洋政府内务部替军阀“修剪外面不好听的声音”,得罪的报人太多,这篇声明一出,没人肯信不说,还挖出了更多的料,说承倬甫跟利用女电影明星与上海的某位“木老板”攀上了关系,还跟日本人来往密切。承倬甫又写一篇文章登报,说这位不是日本人,是台湾人,那还是中国人,是通过正当途径来上海投资建造电影院的。连关夫人都看出来了,在饭桌上跟关洬说,可见六哥儿手里是真的没有实权了,不然哪会沦落到在报纸上亲自跟人打笔仗?
“实权没有,油水大概不会少。”关洬对此只有冷笑,“于伯焘也算对得起他。”
他说完,也不等关夫人再回应,就站起来说吃饱了。留下关夫人一脸茫然,最后只能拉着霞珠感慨:“小时候多好的两个孩子,怎么闹得这样……”
话讲到这里,就又看了陆归昀一眼。于是陆归昀这饭也没法吃了。
关夫人不知道承倬甫去苏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一开始承倬甫还在南京任职的时候,关夫人高兴得不得了,常派霞珠去叫他过来吃饭,只是承倬甫从来都是趁关洬不在的时候来。后来关夫人也看出来了。陆归昀私底下跟关洬说,娘以为是承倬甫跟她有事儿,才跟关洬闹不开心。娘虽然不说什么,心里还是觉得陆归昀“不是个老实的”。陆归昀满肚子的火,只冲关洬发——“你们俩是一个接一个往我脑门上扣屎盆子啊!”
关洬对此只有缩起脖子挨骂的份。好在不久之后承倬甫就调去了上海,总算免了这一份尴尬。不过他还怪有“孝心”的,时不时地给关夫人写信。关洬不情不愿地从母亲那里听说,承家二姐的婚离掉了,带了四个孩子回了娘家。偏偏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年杳无音讯的吴玉山又不知道从那个角落里蹦了出来,要来抢儿子。承倬甫焦头烂额地回了一趟北京——现在是北平了,把他那一大家子干脆分家分掉了。有孩子的姨娘呢,自己去跟着女儿女婿过,没孩子的呢,他给一笔钱,打发了算完。住了这么多年的宅子,他出钱买下来,给大太太养老。最后只把承齐月和元纵一起带到了上海,离吴玉山远远的。
“你别说他油水多。”关夫人替他算了一笔账,“六哥儿不容易的。到底是没有亲娘的孩子,他那些个姨娘,名义上都是长辈,其实一个个只知道趴在他身上吸血,哪怕有一个替他的终身大事操过心,他也不至于这么大了还是孤家寡人。”
关洬听到这里就又想站起来,被陆归昀一个眼神瞪住,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坐在晚餐桌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敷衍他娘:“嗯。”
关夫人认为关洬对于承倬甫太严苛了。要说“油水”,其时的南京政府无人不贪,于伯焘也不见得手里干净,关洬心里是清楚的。他又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腐败问题。前前后后写了三四篇文章,传播得很广,半分未留颜面。因而在学生之间很受欢迎,但是给关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中央大学的学生自己创办了一个“哲学兴趣小组”,原本请关洬来指导,这几篇文章传播出去之后,先是校方勒令关洬不能再去“指导”小组,然后关洬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都被查了一遍,要看这到底是个“哲学兴趣小组”,还是关洬有“另立||政党”的意思。关洬不禁为这个罪名之大而感到惊异,随后于伯焘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请他吃饭,绕来绕去,就一个意思,湘赣那边很把他这几篇文章当回事,拿来攻讦南京,现在有人对关洬很不高兴。
“这算什么借口?”关洬不以为然,“有没有我的文章他们都有话讲,你们要堵我的嘴也该找个更好些的理由。”
于伯焘脸色就有些为难,又搬出关洬曾经写的一篇反对在上海搞流血肃清的文章。因为当时他人还在普林斯顿,稿子寄回来需要时间,后来考虑到时局,报纸没有刊登这篇文章。他低头看了一眼,看见这篇稿子是他的笔迹,也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字,难得是他独自写完,甚至连誊抄都没有让劳烦陆归昀的,这说明他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的分量。关洬只是没有想到,如今手稿会由于伯焘拿出来还给他。
“于兄,这是什么意思?”关洬的语气还是很平静,令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威胁?还是示好?又或者兼而有之?
于伯焘挠头又叹气:“适南,说话的时候,还是要考虑立场问题。”
关洬:“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是搞学术的,不搞政治。我两头都不站。”
“这年头没有两头都不站的人。”
“我同样写过文章,说俄国人插手太过。”关洬提醒他,“那一篇可是刊出来了的。”
于伯焘又一次长长地叹气:“适南,我是为你好。”
“是为我好,还是来给我下最后通牒?”
一顿饭至此不欢而散,自那以后,直到关洬被捕,于伯焘再也没有跟他有过来往。@无限好文,尽在晋江文学城
后来回望,关洬才明白他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当时还远远没有到要给他下“最后通牒”的地步,于伯焘也可能真的是为他好。学校里的“哲学兴趣小组”曾经被要求解散,但是校长跟教育部据理力争。关洬继续写文章发表,谈学术自由之可贵,引得学界诸多附议,最终恢复活动。承倬甫是在那位“木老板”家里的饭局上听说了此事,一起吃饭的还有南京来的孟部长。那篇手稿又被拿了出来,被孟部长笑着推到了“木老板”面前。
“张口闭口流||氓,说得真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