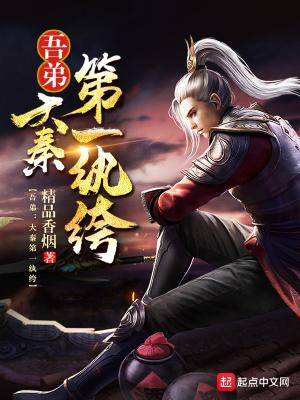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风露立中宵是什么意思 > 第3章(第2页)
第3章(第2页)
承倬甫重新睁开眼。他醒了,但他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半晌,只是问:“谁跟你说的?”
关洬:“詹姆士。”
然后他顿了顿,又回过头,用一种极为神秘的口吻对承倬甫说:“他还说,大清上下,英文最好的人不是我阿玛……是你阿玛。”
洋先生欣赏学生的早慧,对他知无不言。他说二十多年前他到中国的时候,六王爷声势如日中天,正大办洋务。他们这些外国人进入大清,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总理衙门,而当时总理衙门的重臣,正是承廷贞。
承倬甫对此只有沉默。他想假装他早已知道这些事,好像在关洬面前暴露出对父亲的一无所知就等同于羞耻。
关洬一无所察:“他说你阿玛还会法文和德文呢!”
承倬甫突然推了他一把:“你回自己床上去睡。”
关洬:“六哥?”
但是承倬甫翻过身去,把被子一掀,盖过了自己的头。关洬没有走,他已经忘记了白天在为什么事情而生气,像只小猫崽似的,蜷缩在承倬甫背后,就这么睡着了。承倬甫听着他均匀的呼吸,自己却再也没有睡着。后来呢?他很想也去问问詹姆士,也许洋先生会告诉他为什么父亲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承倬甫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一句外语,什么英文,法文,德文……从来没有。他阿玛仇恨一切洋人,但他允许承倬甫来学英文。后来他翻了个身,面朝天仰躺,没有吵醒关洬。外面的天渐次亮起来,承倬甫就这样睁着眼睛盯着慢慢清晰起来的床顶和木梁,心里想象着父亲和詹姆士用英文说话。他们发出的声音古怪而又圆润,像一颗颗珠子从嘴里蹦出来,逐渐铺满了整个房间。
*
黑牢里有一条长长的过道,每次有人走过来的时候,脚步声就会形成拖拖沓沓的回音。时间长了,关洬已经能够分辨每个人的脚步声。一声轻一声重的是那个叫杨阿林的跛脚,他心肠最歹;几乎没有声音的是小柳子,最年轻,也最好说话。那个又重又慢的脚步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正侧卧在勉强可以称为“床”的草席上,身体蜷缩,忍耐着噬人的胃疼。在典狱长敲门之前,他已经知道来的是谁。关洬爬起来,极力作出如常的样子,挺直了背。
典狱长站在门口,扫了一圈,看到他又没动过的饭菜,冷笑了一声,已没了劝服的耐心。他手里又提着一个包裹,还是方方正正的,这回比上次的饭盒大,看起来也更重一些,放到桌上的时候,发出了沉闷的一响。关洬抬起头,无声地用眼神询问典狱长。
“承六爷又来了,”典狱长了然地笑笑,“还是不见?”
关洬垂下眼:“不见。”
“关先生,关教授,”典狱长拖长了声音,有些讽刺地叫他,“你这又是何苦呢?承六爷是什么人物?你们这份交情,别人求还求不来呢……”
关洬厌烦地别开了脸,不愿意听。典狱长愣了一下,自讨没趣似的苦笑一声:“行,算我多事。”
关洬指了指桌上:“这是什么?”
“书。”典狱长说得简单,“我跟他说,书你不会不要的。承六爷说,你没写完的书稿他也替你整理来了,一并的参考典籍,他都去问过了你学生,能想到的、能找到的都在这儿了,若是还缺什么,你再开口。”
关洬咬了咬牙,呼吸急促起来。典狱长说得对,书他从来不会不要。身陷囹圄,他唯一有的就是书了。但他因言获罪,当局许他狱中读书已是宽限,要继续写文章那是万万不能。那份书稿他的学生们已尝试多次,没有一次能越过审查送到他手上。
他撑着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走到桌边。布包被掀开,昏暗的灯照亮了最上面的一本手稿,封皮已经有些卷边,但上面的字迹依旧端正秀丽,写着“中西哲学通史”几个字。下面是两个并列的名字,关洬,陆归昀合著。
关洬闭上眼,仿佛那字的笔锋都是利刃,一刀一刀割碎他的心。
典狱长还在说话:“你得谢谢承六爷。”
关洬:“我是要谢谢他。”
他话中的讽刺太过明显,没有任何被误解的余地。典狱长冷笑了一声,嘟囔了一句“不识好歹”什么的,重新把门锁上,走了。
关洬深吸了一口气,把《中西哲学通史》的手稿拿起来,小心的抹平了卷边的封皮,然后反扣在了桌上。他的胃抽痛得更加厉害,但他尽力忽视,一本一本地检视承倬甫送来的书,全是外语的。关洬实在没有忍住笑意。杨阿林和小柳子大字不识,让他们递话去找中文的书都常常出错,更不要说这些外语书,但这正是他最需要的。翻到下面,还有承倬甫的字条,夹在一本装帧极新的书下面:“听闻德国有奇人名曰Heidegger,其言近年盛于欧罗巴学界,辗转寻得一本,猜你会感兴趣。若德文有困难,可花些时间自学。”然后便是一本德英辞典。
关洬发出了笑声。这间囚室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一时令那笑声尴尬得无处落脚,只能在囚室中左右盘旋。
然而包裹竟还未见底,关洬把厚得能当枕头的德英辞典拿起来,发现底下还有一张字条,还是承倬甫的笔迹:“若实在学不会,切莫为难。狱中清苦,读书自娱,万望保重。”
关洬把字条掀开,看到了包裹下面最后一本书,硬皮封面上露出几个烫金的字母,UncleTomsCa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