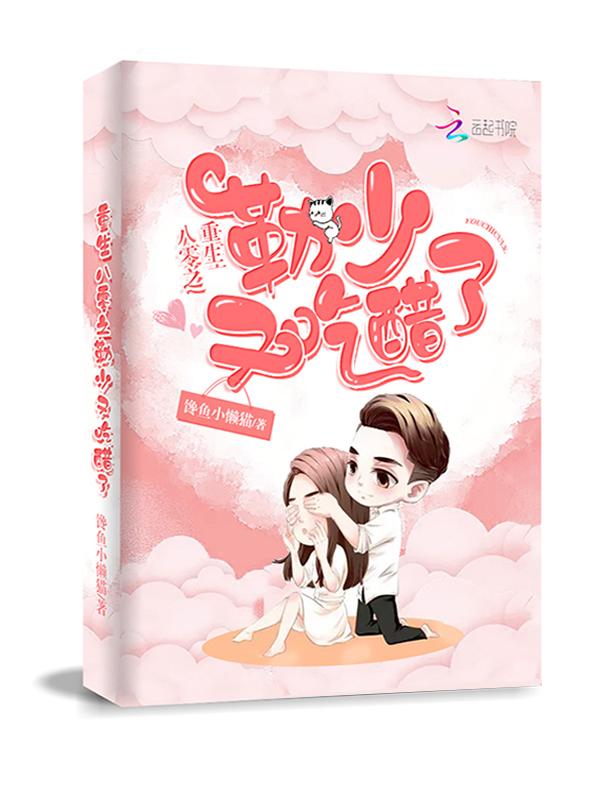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神笔马良是哪个年代的人 > 180190(第24页)
180190(第24页)
钱颂安笑道:“现在系里的确还没定下来,大家想去哪儿?”
有喊胶州的,有喊姑苏的,大半是想看海或者看园林的,闻慈也跟着喊:“去画海!”然后又想起一桩事,戳戳袁韶,“春季写生大概得去多久啊?”
“一两个月吧,”袁韶道,“国画系的通知是下周去五月底回。”
闻慈放下心,看来不至于耽误婚宴。
一趟大课的油画写生结束后,闻慈坐得肩颈酸痛,她起身活动了下,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回学校,当然不是能休息了,而是等下还有一堂讲座。
美院的讲座不少,有本校的老师教授,也有发挥人脉请来的大家,每次一开讲座,基本上都会坐满礼堂,甚至还有许多校外的在野画家,也会一并来听。
一趟讲座时间也不短,等结束后,天也就暗了。
在食堂简单吃两口,回到家,抱着富贵亲了半天,闻慈坐到书桌前。
吸饱墨水的钢笔拿在手里,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纸面光洁,白惨惨的。
写什么呢?
闻慈冥思苦想下一本绘本的主题,从十二生肖想到古代神话,从现代魔法想到西方巫术,众多思绪从她的大脑表面划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可以画,但她不是很想画。
有没有什么能激发她此时创作欲望的呢?
想着想着,她把久久未动的钢笔扣上盖子,掌根托腮,目光不知不觉落到一旁的富贵上,猫是一种很好的载体,不知道是不是她接受的文化影响,天然与魔法、奇幻、女巫这些名词连接。但画女巫的绘本很多,她不觉得自己能开创出什么绝妙的新意。
哎,想不到。
呆坐在桌前两小时,虽然没构思出什么东西,但垃圾篓里的废弃纸团却多了好几个,闻慈把手里这个画了乱死八糟线条的纸张揉成一团,稳稳丢进垃圾篓里。
她看看手表,还是决定明日再构思。
第二天只早上有一节课,上完后,闻慈和乌海青一并去附近的邮局。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乌海青接过去,照着上面的数字拨电话,拨号转接的过程通常是要等一阵子的,闻慈左右看看,口有些渴,于是指了指对面的供销社,“我去买个汽水,你要不?”
乌海青点头,电话那边已经通了,他赶忙说找美影厂的动画师年君。
闻慈小跑出邮局,在供销社买了两瓶汽水,这汽水瓶要交付押金,喝完来退瓶子的,她旁边一个老奶奶正买肥皂,拿出一张工业券。虽然改革开放,但票券时代暂时还没有结束,只是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物资没有那么紧缺而已。
今年年初,国内已经有了合法的个体户,在商业局领了营业执照,可以大大方方开店。
付了几毛钱,闻慈拎着两瓶汽水回邮局,见得乌海青杵在柜台前面打电话。
“对对,闻慈跟我一起过来的,她买汽水去了——诶,她回来了!”乌海青朝闻慈招招手,闻慈没想到这回电话通得这么快,赶紧跑了过去,“接上了?”
“年君正好在通讯室拿包裹呢,巧了,”乌海青笑道。
汽水瓶刚才在供销社打开了,闻慈递给乌海青一瓶,自己喝一瓶,四月按理来说该是凉快的,这两天却有些闷,总想让人喝点冷的刺激的,从喉咙到胃都痛快一下。
闻慈不急,等乌海青和年君先打电话,自己喝着黄澄澄的橘子汽水。
说要主动打电话的是乌海青,但实际上,说不了多少就没话了。
关心的、煽情的话,他们俩说不出来,工作上的问两句就行了,问多了跟当领导似的,可也不能光问最近吃什么、天气怎么样吧,因此,打不到五分钟,乌海青就开始瞄闻慈了。
闻慈一瓶汽水都下了肚,指指话筒,小声问:“给我?”
乌海青连忙点头,交接完话筒,拎着汽水瓶子灌了一大口,“痛快!”
闻慈把话筒贴到耳边,笑道:“好久不见啊。”
年君刚才和乌海青聊的几分钟,已经把他们俩近来发生的事都听得差不多了,听闻慈过来,先是恭喜了她这段时间的成绩,尤其是全国美展的。
闻慈笑着说:“你现在也干得很好啊,《哪吒闹海》我看了,拍得特别特别好。”
年君揪着包裹的尼龙皮儿,听到两个“特别”,心里也忍不住高兴。
他嘴上克制地道:“比不上你,你现在全国都出名了,现在画油画的谁不知道首都美院的闻慈?我跟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她夸过你好几次,说你比当年还厉害了。”
闻慈“嘿”了一声,“这人往高处走,当然得不断进步啦。”
说了几句,年君又说*:“我现在在美影厂待得还不错,画动画很有意思,我觉得比水彩国画有趣,这边的动画师基本上也比较年轻,之前那个《哪咤闹海》,主要框架和人物设计是大师们做的,我们就画画分镜,合作起来也不费事儿。”
闻慈好奇地问:“这拍一部美术片得花多久啊?”
“怎么着也得一年半载吧,”年君道,他回忆着上回的经历,“《哪吒闹海》是78年5月立的项目,又是外地写生,又是实景取景的,一直到79年国庆那会儿才制作完。反正美术片画起来其实很费功夫,一个剧组好几十个人,各有各的活儿。”
闻慈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你暂时就打算画动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