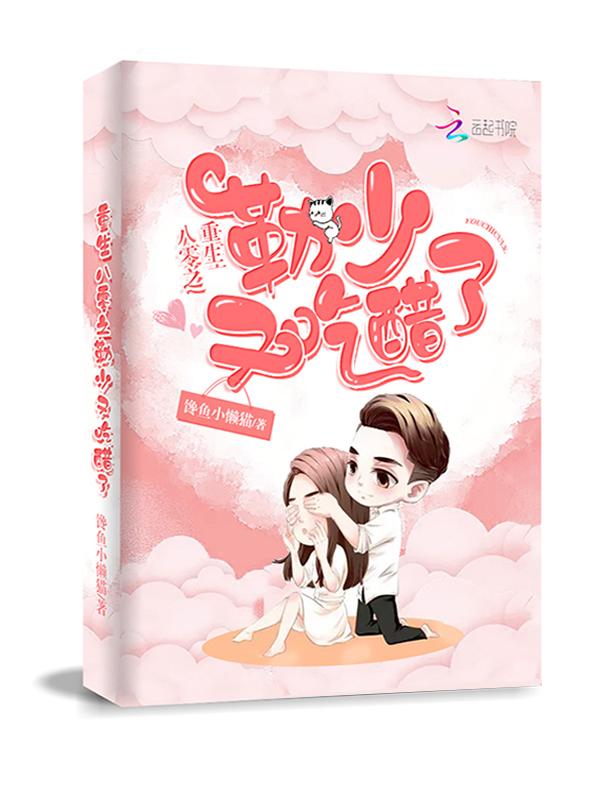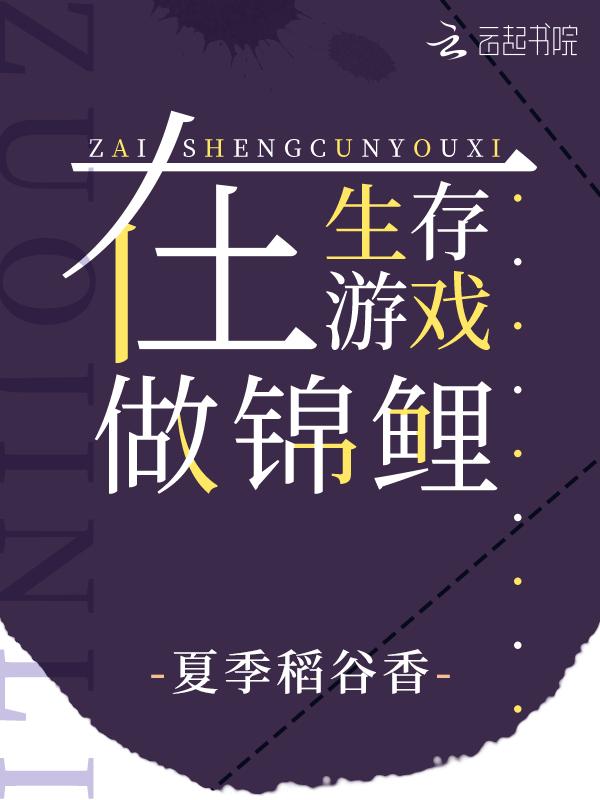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神笔马良是哪个年代的人 > 190200(第26页)
190200(第26页)
解说员走过去要介绍,他们摆摆手,是自己游览的意思,的确,有些人更喜欢发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欣赏,闻慈没有往上凑,照样在不远处背着手看画,只是偶尔转头看一眼。
再次转头时,几位老人停下脚步,是在《野象》面前。
“很惊人的画作,”带着皮质手套的老人惊叹。
“闻、慈……我觉得未来还会认识这个名字,”另一位拄着木头手杖的老人低语,他向后退步几米,好把这幅庞大的画作尽收眼底,离得远了,细节看得不那么清晰,但整体感官却更加冲击眼球。
他们朝解说招手,低声问:“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幅油画吗?”
解说急忙走过来,这是今天的第一“单”,他神色认真,专业地讲述起早已倒背如流的介绍,从创作背景、创作概念一直到画家本人,几位老人专注听着,时不时点一点头。
“很独特的创意,”他们感叹,“请问展馆里还有她的作品吗?”
解说摇头,“只有这一幅,”他说着,下意识看了不远处的闻慈一眼,几位老人也随之看过去,发现是个看起来年纪很小的亚裔姑娘,打扮时髦,神色大方,朝他们礼貌地一笑。
几位老人并没太注意,很可惜地道:“没有其他作品啊。”*
解说犹豫一下,还是说:“那位就是画家本人,你们要和她聊一聊吗?”说着,右手侧掌指向闻慈,神色相当尊敬。
几人愣住。
“她,”手杖老人惊诧地扭过头去,又看了眼闻慈,“哦,天呐,她成年了吗?”
走过来的闻慈恰好听到这句话,她一边伸出手来,预备握手,一边微笑着用英文说:“我今年21岁。”
几位老人纷纷跟她握手,神色还是不可置信。
“这部美丽的油画是你的作品?”手套老人问。
闻慈颔首,“上一年时,我去华夏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写生,那里有草木丰沛的热带雨林、丰富的野生动物,画上的象群就是在那里生活的——它们生机勃勃,不是吗?”
“是的,是的,”老人忙点头,感慨道:“真是想不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闻慈本来脸就圆,对于欧洲人来说更显得稚气,有些吃亏。
她毫不意外,微笑着道:“生命向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诸位愿意,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它们背后更丰富的故事。”
他们停驻下来,听闻慈娓娓道来。
“象牙的猎取是一项非常残忍的行为,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偷猎者往往等不及大象自然老死,他们将活生生的大象砍掉半张脸——象牙和大象的头骨相连,为了获得更多的象牙,他们猎杀整只大象。而侥幸没有被杀死的大象,因为失去象牙,也几乎无法在野外生存。”
现在国际上各国是有动物法的,但基本上都不完善。
戴手套的老人捂住了自己的嘴,睁大眼睛问:“不是古代的象牙留存下来的吗?”
“您说的是猛犸象吗?的确有很多人去寻找永冻层里的猛犸象牙,但也许因为数目太少,品质与现在的象牙也不同,所以完全没法满足市场,猎杀仍然在存在,”闻慈说。
“天啊,”手杖老人喃喃,“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他看着油画上在河边打滚的小象,很难想象,它有朝一日会被砍掉脸、生生拔出象牙……光在脑海中构思一下这个画面,他就打了个寒战,觉得毛骨悚然。
闻慈道:“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使用象牙制品的喜好,这幅画的最初,也只是想让那些对此有收集癖好的人看到,象牙从它的身体剥离之前,来自于一种活生生的、温顺友好的生命——象是温厚的动物,体型如此庞大,却只食草木。”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恶,实际上都是由上层者创造的。
原本只是一幅震撼美丽的丛林动物油画,现在再看,却好像染上了一丝挥之不去的悲壮和哀痛,几位老人望着画上活泼玩水的野象,良久说不出话来。
善良人类的共情能力,往往会对同类的恶行感到愧疚。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人低声喃喃。
“我希望它是一部能引起反思的作品——哪怕只得到一点点注意,”闻慈低声说。
这幅画后,几位老人继续向前,闻慈驻足片刻,忽然觉得有些伤感。
后面的参观者陆陆续续的来,油画区在刚进门不久的位置,大家总是能看到这幅震撼庞大的野象油画,解说渐渐忙不过来,闻慈随机挑选一些看了很久还面善的——靠直觉。
人似乎有种磁场,第一眼看到这人,你就知道能不能聊得来,这人好不好相处。
这项能力闻慈向来掌握得不错,她挑选中的参观者,有女有男,有年老有年少,底色都是较为善良的人,光是听到象牙的猎杀,就有人眼眶湿润起来。
“天啊……我家里还有两个象牙镯子呢,”一位女士捂着嘴说。
“只要未来不再创造流通市场,那您已经是一位正义善良的人了,”闻慈说。
能意识到问题,已经是拥有非常难得的共情力了。
闻慈不知道其他画家面对这么多人,会不会因为语言不便变得社恐,她自己倒是如鱼得水,方方因为用不上翻译,帮忙解说去了,小小的油画区俨然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