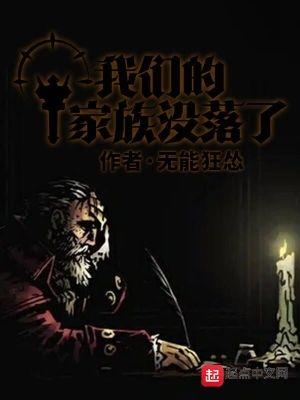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渣男吃干抹净就抛弃了我 > 第 4 章(第3页)
第 4 章(第3页)
一时间巷子里只剩下她呼救的惨叫。
终于,她受不住地松了口,“你放过我吧!那三千两都给你!”
吴大牛一口唾沫啐在她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外衫上,揉着手腕,双手肿胀得通红,“昨日我说过什么?她们能帮你几时?赵春花,你就是一条贱命,认了吧!”
他揪起来她的发髻,拍拍她肿胀不堪的脸,声音冷得刺骨:“三千两,饶你一次。要是不想死,明日,五千两。”
吴大牛将她往地上一掷,将那锦袋甩在她脸上,扬长而去。
赵春花眼前被凌乱的头发和血糊住视线,艰难地爬到门口,挣扎着起身关门,放下门栓,才敢长舒一口气,麻木地落了泪。
“林蕙姐,尔茗姐,救救我……”
晚些时候,林蕙穿着一身粗布的男装,赶着送酒的驴车,踩着县城关闭城门的时辰进了城,慢悠悠地往城南去。
黑市的赌场在日落时分才开门迎客,等她停了驴车将酒送进赌场的后门,正好瞧见吴大牛往前门去。
她挪了挪头上的布巾,散些碎发遮住眼睛,弯着腰、低眉顺眼的模样同吴大牛擦肩而过。
林蕙粗着嗓子和后门的守卫报备:“郊外无忧庄子,送酒。”
那守卫眯着眼看了看她,又看她身后驴车装得满当当的酒缸,谨慎地过去掀开了酒封闻了闻,才减了警惕:“瞧着你脸生。怎么,你们老刘头今儿病了?”
“他今天腹痛,托我过来送一趟。”她闷声答。
那人挥挥手,放行。见她拉着驴车向往里进,厉声阻止道:“哎!不懂规矩!车,不能进,酒一坛坛往里搬。”
她连忙招呼身后的伙计一同照做,在驴车的酒坛即将清空时。赌坊前门传来消息,说是忽然来了个贵客。
黑市后门原本森严的守卫,抽走了一半的人去前院盯梢。
恰逢其他的货商也到了,十几家的木板车堵得水泄不通,一人一物送进去,严查携带利器。同赌场合作供应的皆是老店,仆从们自顾自地忙着见怪不怪,进进出出。
谁也没注意某家送酒的小厮,似乎少了一个。
落日的余晖淌在沈府的湖面,风一吹,荡起一阵阵金红的波光。
湖面铺着碧叶粉荷,西边一座小亭,苏尔茗手捧书卷,品着荷叶茶,闲适淡雅。
她目光自书卷中恋恋不舍地离开,看着那天边的晚霞,轻声问了句:“芸娘,现在什么时辰了?”
“夫人,刚过酉正。”
她想了想,林蕙应该才进去一刻钟。
苏尔茗端起手边的茶杯,浅浅抿了一口,心中盘算着她事先联系过庄子上的人脉,专门有人做指认抽老千搅混水的生意。
那人说,只需要派人去南市的茶肆吩咐一句,“要半斤茶酥,不要盐,要素油”,便立刻会有人去盯,当日钱来路不正的“贵客”。
她撑着下巴看着近日时常开始发呆的芸娘,无声地笑了笑,出口打断:“芸娘。”
“……夫人。”芸娘怔愣一下,才应声。
她眼里并未有责怪,揉着自己干瘪饥饿的肚子,像个小女孩一样撒娇道:“芸娘,我想吃南市门口的那家茶肆的茶酥。”
芸娘微微皱眉,温声提醒道:“夫人,等下老爷便要回来用膳……”
她伸出两根手指,扯着芸娘的衣袖晃了晃,颇为委屈:“我吃完饭喝茶的时候再吃,就要半斤,不要盐,要素油。”
芸娘被她磨得没办法,只得应声迈出湖边小亭。
走没两步,迎面遇到了回府用膳的沈万金。
苏尔茗心头一揪。
芸娘福了福身,不知和沈万金说了些什么,他立刻拧眉迈进了小亭,声音极为不悦,命令道:“马上用膳,吃什么茶酥?”
“芸娘,不准去,立刻布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