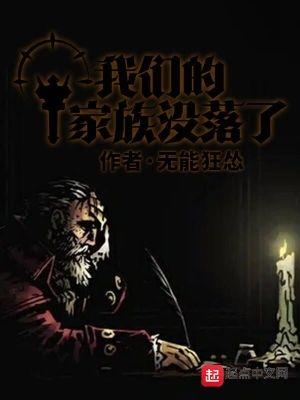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恨 > 12回宫(第4页)
12回宫(第4页)
先前还扮作少女,如今是妇人模样,外头只道他新寡,称一句“祝夫人”。
祝久望向琉璃窗,隐约看见半张脸,露出丝缅怀的笑。
“安平若活到现在,想必已嫁人。”
旁边侍奉的云苓闻言,手抖了下,只恐殿下伤心。
当年梁王满门覆灭,先帝不允她救安平翁主,姜云翊知道后,插手此事。
半月后,他说安平早在兵败当日自刎,但她有一兄长,平素于山中清修,扮作宦官逃出生天。
真是“福大命大”。
姜容婵望着浓妆艳抹的脸,心底戚然,天子派的人不好糊弄,哪怕小宦官也要搜身。
眼前人虽有喉结,却已是阉人。
祝久却无悲戚,躬身一拜。
先谢罪再陈情。
“臣无意引殿下垂怜,宽宥过失,过往无须再提,容臣阐明税金偏差缘由。”
“你先起来。”姜容婵头疼,“我又没责怪你。”
祝久直起身,蓦地想起什么。
“陛下会来么?”
姜容婵知他怕皇帝,“他还未下朝。”
再者,下朝后,那些老臣八成要拦住皇帝劝不停。
“阿姐忘了,今日休沐。”
不知何时出现的少年言语带笑,拨开珠帘,拇指大的圆润珍珠只发出轻响。
沉静柔和到极处,天青锦衣也如流华泄地。
皇帝望向祝久,眸中无半丝不屑,径直坐在姜容婵身侧,微微颔首,堪称礼贤下士。
“久闻祝夫人虽非内史,却是高阳财库丰厚的大功臣,若非不便,朕委实想命治粟内史拜祝夫人为师。”
祝久脸颊抽搐一瞬,脂粉险些往下扑簌簌掉。
他谦卑谢恩后假笑,姜云翊最是狼心狗肺。
对外戚张家是白眼狼,对姜容婵就是护食的狗。
殿下就是那根香气四溢的肉骨头。
祝久双膝向后挪,尽量忽略皇帝这尊煞神。
“殿下,去岁至今,财库充盈异常,实因商户纷纷献纳,商户重利,其中必有蹊跷,臣欲带人探查缘由。”
“关乎财税,朕可以从廷尉府调人手协助。”皇帝眼底泛冷,“朕方才看了眼简牍,也万分好奇。”
祝久心道不妙,姜云翊还是那个德行。
见不得有人跟殿下相处,哪怕他是着女服的阉人。
皇帝慢条斯理,指尖轻敲桌案,每一声都像恐吓。
“去岁才盈余这么点,朕以为赐给阿姐的铜山不翼而飞了。”
姜容婵发觉祝久额头渗冷汗,掌心下意识地,碰到少年置于膝上的手背,轻拍了两下。
皇帝钝刀子似的质问戛然而止,原本被怒意冻硬的唇角倏然变软,隐约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