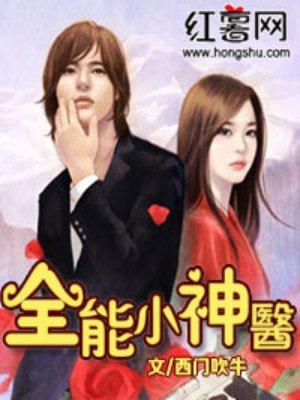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雪落下来扩写句子 > 第52章 52 半是甜半是酸(第3页)
第52章 52 半是甜半是酸(第3页)
周边传来短促的笑声,张某某的脸瞬间气成酱色,楼清知对其他人无感,只感觉陈元弋捏了他的胳膊。
柳飒往李时阅身后躲了躲,嘴角已经压不住了,李时阅也很难绷,主动打圆场道:“东展区有许多老收藏,咱快走吧,再不去要被订完了。”
楼清知点点头,看都没多看那人一眼,“走吧。”
小小闹剧将要落幕,不甘心的演员没博够关注,冲着楼清知的背影叫嚣道:“老玩意这不现成就有一个吗?新时代了,谁家还有姨太太呀?楼二爷,你说呢?”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转移到楼清知身上,如芒刺背。
楼清知站定,风起,浑身爬过一层冷电,眉心轻轻地蹙着轻颤。
与他有关的话题——能力是其次,容貌是噱头,唯有身世总沦为谈资。
南北差异显著,南方文明驾着火车飞速前进,北方则在顽固的世风下安睡,直到火车撞碎风雪才撼动了它的固执。
新时代的车轮抵在大宅院的门槛上,老一辈人的观念根深蒂固,早已不做严格要求,楼铭瑄站在时代的浪头自然不会纳妾,楼清知更是连婚都不想结,妥协至此仍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就因为他家还有其他姨娘,而他,托生在姨太太肚子里。
“以前是叫庶子吧?害,楼二爷还是占了便宜的,放到现在该叫野种了哈哈哈哈……”
楼清知站在原地,被好多双眼睛刺穿,他一向能言善辩,此时却哑了喉咙,陈元弋要扑上去,楼清知按住了他的拳头,“别动。”
一提到身世,他总是不知如何反抗的。
他有错吗?必然没有,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好落个清净。
错的不是他,他却无力为自己辩解,不论如何说,他都是格格不入的异类,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而他是无可辩驳的庶子、是野种。
诸如此类的言论从小听到大,他的哭闹无人问津,楼臻不会安慰他,大夫人会说他不懂事,楼铭瑄只是摸摸他的头跟他说“没事的,长大就好了”。
骗人的,从来没有好过。
楼清知回首看向嚣张的某人,他想起来了,这位是张越珉,刘昭帮他办商标资质时得罪了他哥,那时楼清知病着,早把小破事忘了。
张越珉见他默然吃瘪,咧着嘴走近,手指戳着楼清知的领带夹,烟草气扑面而来,“新时代一来,就被赶出家门了吧?什么楼二爷,丧家犬还差不多,啧,这脸长得着实不赖,毕竟你娘是出来卖的,不好看谁买啊,龙生龙,凤生凤,头牌的儿子卖什么都得心应手,你说是不是?”
说罢,那脏手竟往楼清知脸上凑,一只手死死扼住了他的手腕。
楼清知迅速反拧,张越珉痛呼一声瞬间跪倒在地,楼清知冷冷地垂眸,一言不发。
他看向身后气得直冒青筋的人,终于松开了陈元弋的手。
陈元弋豹子一样蹿上去,打过铁、抗过包的双拳重重砸在张越珉的臭嘴上,他的双臂能抗两百斤,也能替二爷抗住流言蜚语——扛不住就打。
楼清知面容清冷,不见愠色,低哑地叮嘱道:“往死里打。”
得了命令,陈元弋揪着张越珉的衣领,奋力将人砸向窗外。
玻璃窗碎出彩虹,映在楼清知脸侧,半张绚烂,半张落寞。
他擦擦手,无可辩驳,那便撕烂别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