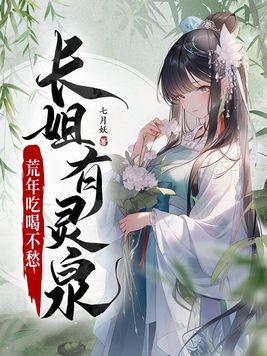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易卦正解 > 17夭儿17(第2页)
17夭儿17(第2页)
-
次日。
天还未大亮的时候,雨停了片刻。雨后的初春凉意袭人,空气中弥漫着潮气和土腥气,夹杂着草木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棺材铺的后门在此时被拍响。
那响声持续了片刻,姜叔方披着衣裳出了卧房,趿拉着鞋子去开门,嗓音还有些沙哑:“谁啊?”
天将拂晓,晨光熹微,院门打开,门外人影隐约可辨。
是方晏。
方晏一身官服穿戴整齐,笑容腼腆,一手拿着把还在滴水的油纸伞,另一只手拎着几个油纸包,在姜拯面前晃了晃:“秦婶儿昨儿说我,每次来棺材铺都是白吃白喝。恰好今早为了案子之事,要来寻阿舒,我便顺路去隔壁朝食铺子,买了些小食,大家伙儿一块趁热吃。”
“你是秦二娘的孩子,便算是我的侄子,这么客气做甚。”
姜拯接过油纸包,将他迎进院,贺玄听到声响已然起身,靠在门边,挠了挠杂乱的发髻,张开嘴打了个哈欠:“来这么早做什么?又有死人了?”
“贺兄,做人,还是要良善些。”
方晏看着他不修边幅的模样,颇为嫌弃,扬起下巴懒得再搭理他,径直走到一旁尚紧闭的房门前,曲起手指,小心翼翼叩响屋门:“阿舒,起床啦,昨日我派出去的人查到了些消息,可要听听?”
屋内安静无声。
方晏似早就习惯了似的,重复着刚刚的动作话语,贺玄看着他这副谄媚的模样,听着他像是被人捏着的嗓子,翻了个白眼,转身回屋,将木门摔合,发出震天响声。
这声响传进了紧闭的房间,惊醒睡梦中的人。荀舒揉了揉眼睛,在一片嘈杂中恋恋不舍起身:“知道啦,这就来。”
待她穿戴整齐,走出房间时,院中人已坐齐,荀舒到空置的位子上坐好,忍不住问道:“方大人快说,你的手下查到了什么?”
方晏将热腾腾的面片汤推到她面前,简略道:“昨日我令人去王家布庄附近打听,探得两条消息,其一,王家在王福婉前,确实有过一个男孩,只不过那个男孩三四个月大的时候便夭折了,说是染上寒症而死。听周围的人说,王家很疼爱那个孩子,特地将他葬在城外感怀寺的后山,为他层砖造塔。今晨我已着人去感怀寺寻那孩子的尸骨,约莫下午时便能返回城中。”
“塔葬?”贺玄挑了下眉,“寻常百姓家的婴孩夭折,大多用瓮葬,王家却舍得出这么一大笔香火钱,将其遗骸安置在感怀寺中,真是大方。”
荀舒小口咬着香酥饼,口齿含糊不清:“为了安心,花这点小钱又何妨。不过也幸好他们还存了这么一分善心,才能让我们有机会寻到这孩子的尸骨。”
“也是。不知王家人知道这件事,心中作何感想。”贺玄感叹,“那第二条呢?”
方晏道:“其二,那衙役走访了王家布庄的邻居,其中有一人提及,发现赵夫人尸体的那日,他清晨出门时,似乎瞧见一人匆匆忙忙赶回王家布庄,瞧身形像是王福婉。他出声叫王福婉,却见她走得更快,头也不回进了门。”
王福婉竟是天亮后才回的布庄!
荀舒初时惊讶退去,旋即想起了一事,潮州城夜里有宵禁,若无官府令牌,百姓不得跨坊。赵宅同王家布庄分别位于两个坊,王福婉无法在宵禁时返回家,那素梅又是如何回去的呢?
她将这想法说给贺玄和方晏听,几人商议片刻,决定先将素梅押解回衙门,再做打算。
正事聊完,朝食也用得差不多了。吃饱喝足,方晏的目光在荀舒和贺玄脸上来回扫,心中的好奇和疑惑再也压制不住。
他一直忘不掉昨日下午,在赵县令书房中的场景。
他见过不少平头百姓与县令说话,无不战战兢兢哆哆嗦嗦,胆子小的甚至不敢抬头看赵县令的脸,与荀舒和贺玄的表现大相径庭。
荀舒也就罢了,一向视权利如粪土,无论同谁说话都是一副模样,不因是权贵而阿谀奉承,亦不会对乞丐流民流露不屑。可这贺玄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能在面对赵县令时,不惧怕,不恭敬,仿佛只是个生疏的朋友……难道他愚蠢到不知官与民的差别?
方晏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定定看着贺玄:“贺兄,你受伤痊愈也小半年了,救你时,你受了伤,忘记了以前的一些事,如今可有想起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