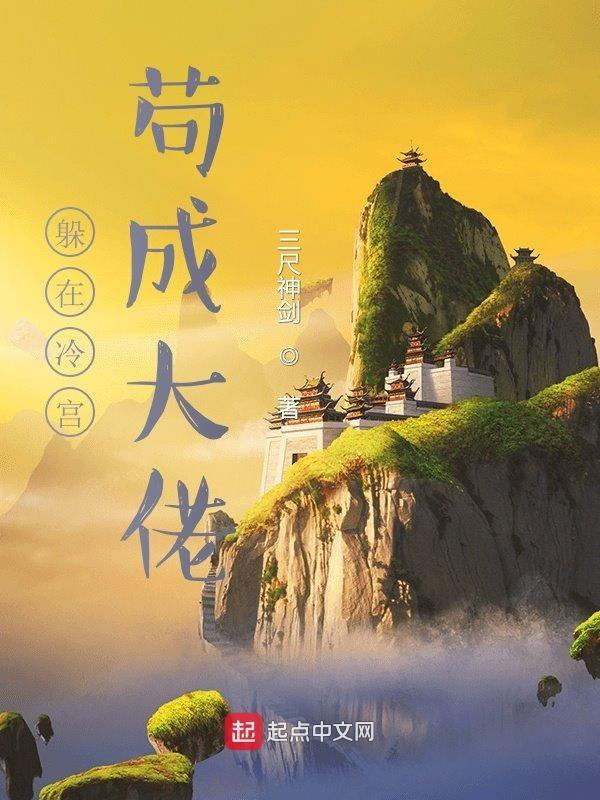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弃犬质子夏鹤风 > 9心渎(第1页)
9心渎(第1页)
她能画出来么,一个月后的比赛。
看着画布上还未完成的肖像,顾乐心里升起一股烦乱。
仅简单铺设了暗部,还未刻画,男人身体的轮廓就这样在画布上袒露。沟壑分明,寸寸引诱人探寻。
她擅长表现光影,顶光照下,打在他无措展在椅子上的身体上,像神吐下来一道神谕。
纯洁又靡丽。
米托拉吉。
顾乐脑子里浮现这个名字。
小时候无意中在启蒙老师的书本上看到他的经典作品,只记得一张巨大残破的人脸,斑驳的纹路从颊边攀援而上,仿佛一碰就要碎成千万片。自此,美丽幻梦般的这张脸就扎在她脑袋里,直到现在。
赤裸的身躯不过是千百年艺术史中一颗点缀,她看了太多,毫无波动。
即便她觉得残破的更美,但也只报以欣赏的目光。
她爱米托拉吉,却不会因他的作品失态。
而此刻家里终于没有嘈杂的吵闹和孩子的哭泣声,顾乐在画板前端坐着,身体里再次涌上一股难抑的潮热。
怎会如此。
像第一次遇见他那晚。
余根生。
顾乐唇边含着这个名字,反复嚼咽。
……
-
自那天去过余根生家后,顾乐就照常去画室。
她和余星童一大一小从午后画到傍晚,然后坐上余根生的电动车回沙南。
她总掂一杯水果茶回家,余根生和余星童则继续守摊。
他们偶尔一起吃饭,闲聊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仿佛那场暧昧的雷雨不存在。
直到今日余根生发现她哈欠连天。
杂面小摊。
余根生指了指顾乐打哈欠的脸,眉头锁紧,粗糙的手指在空气中用力点了点自己的眼睛,然后手掌一摊,做了个“累”的手势。
余星童见状放下筷子,嘴里还嚼着面条:
“顾老师,爸爸问你是不是太累了?”
顾乐顿了顿。
“没有,昨晚写作业了。”
余根生将信将疑。
他目光扫过顾乐,定在她细白的手腕上。竟然有一小块新鲜的烫伤红痕。
他鬼使神差地伸手往前,手指点住那块儿伤。
顾乐下意识缩手。
余根生也意识到不妥,尴尬收回手,继而微微皱眉,眼神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