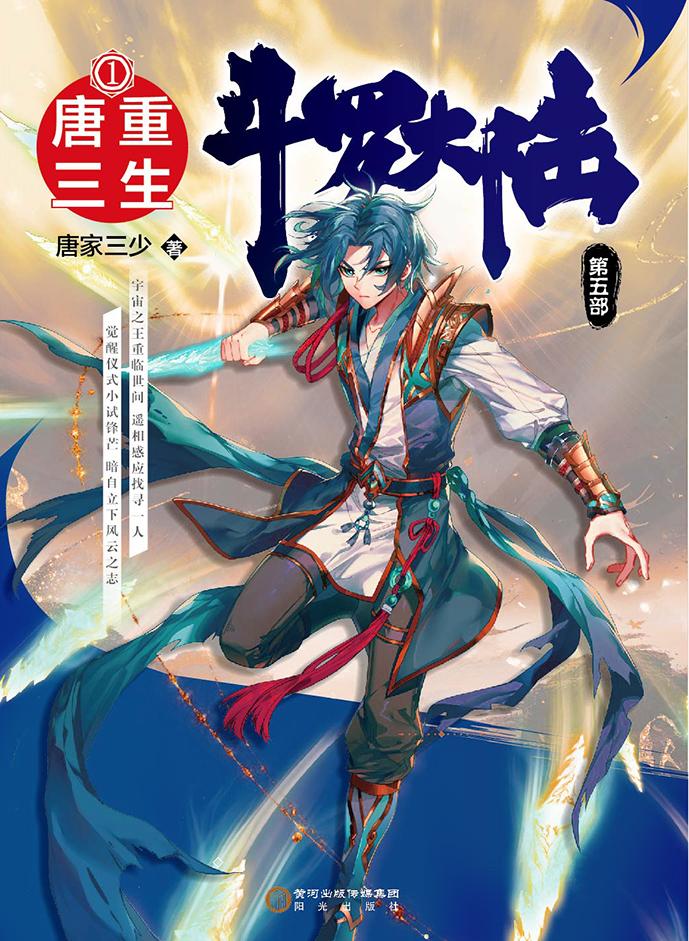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当我们建设大唐 贞观外交官 > 空相护一(第3页)
空相护一(第3页)
今日兵部开会,讨论是否要将思摩调回长安,再换更有威慑力的将军过去。因着兵部尚书尚未到任,会议的主持人是魏侍中,而我作为藩将的“父母官”列席听证。
“我希望大伙客观一些,不要夹带对思摩将军的个人偏见。”魏侍中道。
我循例朗读思摩的履历,他开皇七年生人,如今五十有八,已经降唐十年了。
“思摩将军是个开朗和善、礼贤下士的人。他对大唐的文化很认同,也有自己的思考。鸿胪寺编纂《突厥语商务对话一百二十句》的时候,曾请他做为校对。”
不确定魏侍中有没有在听,他双眼微阖着,像要睡着了:“他是个翻译?”
我回答道:“他在突厥的官职是‘苾特勤’,是个贵族散官,早年间负责突厥的外交工作。”
兵部参会的官员席位间,有人问道:“他从未打过仗?”
“是。”
又有人问道:“颉利因着什么不用他领兵?”
“因为思摩将军长得像龟兹人,不像突厥人,曾经被质疑血统不纯正。”
“那圣人为什么要用他?”
魏侍中一句话问出口,席间嘈切起来。郎中与主事们的窃语算不得窃语,教谁也听得清:“门下省自己画的押,早怎么不驳回?”
魏征没听见似的,抬了抬眼皮望向我:“问你呢,‘斩立决’。”
“当年颉利败北,酋首四散离析,只有思摩将军仍旧追随他。圣人喜爱他的忠诚,因此相信他可以胜任。”
这是江夏王讲与我听的。我来兵部之前去公廨找他,他只交待了这么一句话,便什么也不说了。
魏侍中问道:“你自己相信你说的话么?”
我为什么不相信?
“下官——”
我铆足一腔力气,有满腹争辩的话想要一股脑地倒给他们听,不知席间哪一位同僚冷声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早知道便不该教他们做将军,血海深仇尚不能得报,哪有俘虏为战胜国上阵冲锋的道理?倘若思摩根本不曾真心归附……”
这是什么话?
不论如何,思摩是圣人钦定的三品大将。御下不利是能力问题,隐瞒不报是他作为外族将军畏惧朝廷,何至于质疑他的忠诚?
叔玉打断那人的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是圣人自己说的。你若连这些话都说得出,大唐日后该如何教化四方?”
“魏侍中,下官原本觉得思摩将军可以回来,眼下却实在不能再有换人的主意。”我感激地望了一眼叔玉,陈情道:
“我们的同僚最清楚他,却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若中途换帅,天下人不知会怎样看待思摩将军。请魏侍中考虑礼部的意见,大伙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再惩罚犯错的将军罢。”
“薛郎中,你才来礼部几个月呀,这样快就倒戈了?”
我仍没认出这是哪一个发言的人,听声音,不是方才的那一位。
席间哄笑起来。
一瞬间我灵光忽闪,有些清明了。
原来归降十年,突厥将军仍旧是不被不信任的。这份不信任映衬在每个人的眼睛里,如同草原中夺食的狼与豹,闪烁着愤怒的火光。
如果阿史那思摩值得托付,那么戍边的士兵就不会冒死逃来长安告状。我明白这一点,我此刻僵立在当场,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正是因为我明白这一点。
让我不寒而栗的是,就这一点上,我的内心竟然是认同的。
可身为礼部的官员,我绝不可能有第二个立场了。这些怀疑的、愤怒的眼神不止望向黄河畔的思摩,也望向我。
同僚们看着我,正如同我看着兵部的那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