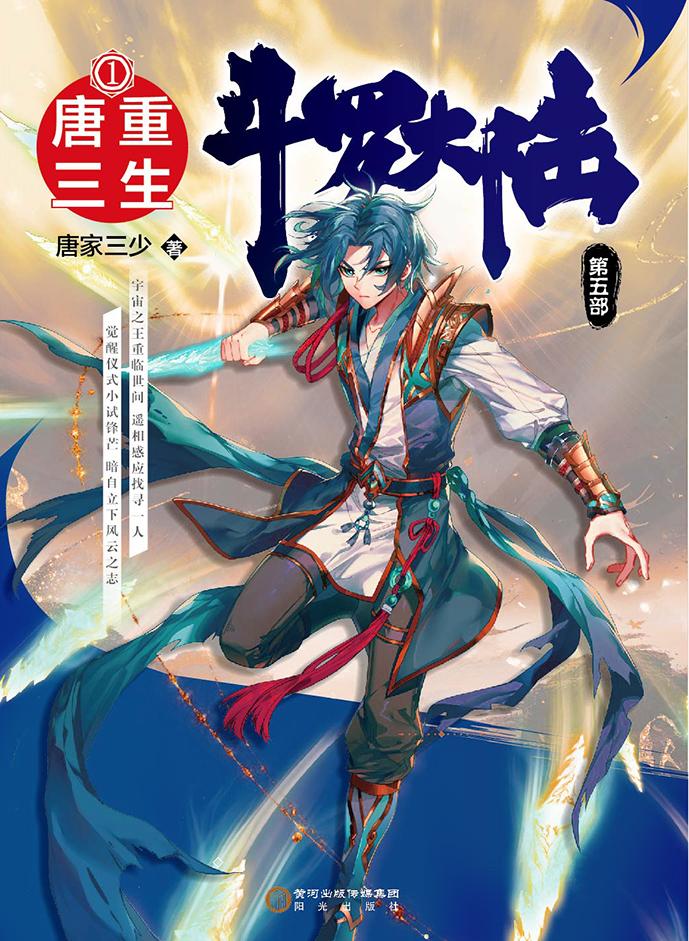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桃花堪折txt > 3040(第18页)
3040(第18页)
梅子酒虽然清甜,倒是酒劲猛烈,李嶙当做梅子汁,自己一人就喝掉了一瓶半,此刻已经有些头晕目眩了,趴在案几旁,能听到元桃他们说话,但是又听不清说什么,能看到他们两个影子,但是又实在模糊,抗不住醉意,两眼一黑就昏睡了过去。
“这……”元桃刚将药水倒在手心,看着昏迷的李嶙,问道:“他也是受伤了吗?”
李绍扫他一眼:“他是喝多了。”
元桃心里鄙夷,将李绍的衣袖再拉高一些,手臂肌肉紧实线条流畅,手腕处尺骨清晰可见,因被马球棍击伤,手臂大片都红肿着,皮肤薄的地方还有渗血。
元桃不敢轻易下手,踟蹰道:“这伤很严重,不叫医师来看可以吗?”
李绍淡然说:“你只管上药。”
元桃将药水在掌心化开,搓热了后,小心的抹在他的手腕和手臂处。
皮肤相接的地方火灼似的,血管胀痛的似乎要迸裂,李绍眉头紧蹙。
元桃说:“是疼吗?”
李绍没有回答,目光一沉,转而问道:“白天有温书吗?”
元桃摇了摇头。
他有一句无一句说:“没耐心了?”
元桃说:“并不是……”
李绍看着她垂着眼帘欲言又止的模样,觉得有意思,少女的心思一览无余,他这会儿颇有耐心,问道:“有心事?”
元桃一怔,望向他说:“奴婢也不清楚。”
李绍只是笑笑。
元桃给他抹药的手停了下来,思考片刻,说:“奴婢有时候会做梦,梦见吐蕃王子宅里的。”
她看着油灯外罩着的那层雕刻的鹿纹镂空铜灯罩,语气沉寂,道:“奴婢想要给刹叶报仇,可是奴婢卑微若蝼蚁,要如何去报呢?奴婢经常想来,就会觉得心中茫然,连带着对于报仇这件事都渐渐失去了执念。”她垂下眼帘,她发现她的心是空的,报仇吗?似乎于她而言又不是那样重要。
她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她和李绍说这些做什么,抿了抿嘴唇,勉强微笑道:“奴婢也说不清楚,兴许是流浪漂泊惯了吧,又是戴罪之身,说不好哪天就被关进了大牢,如同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李绍却接下她的话,问道:“如果可以为刹叶报仇,你能做到何种地步?可愿意搭上自己性命吗?”
元桃一怔,复坦诚说:“奴婢不知道,奴婢有时实在是怕死。”
“那如果是为我呢?”
元桃略感诧异,片刻后问:“忠王您是什么意思?”
李绍错开她的目光,语气仍平静如常:“如果是为了我做事,你愿意做到何种程度?”
元桃思考片刻,火光映照着她的脸庞,看起来是那样清澈美丽,她是干净的,像是枝头未绽放花骨朵,又像是方才脱离窠臼的雏鸟,蓦地,她想明白了,正襟回答:“只要不伤及奴婢的性命,奴婢愿意试。”
李绍收回了手,放下袖子掩盖住手臂的伤痕,语气淡极:“你不必庸人自扰,亦不必思考是否要为刹叶报仇,更不必去思虑明日会身在何处,是否要继续漂泊流浪,至于戴罪之身,那就更无足紧要了。”
元桃心猛一沉,明亮的眼睛怔怔望着他,烛火“毕剥”作响。
李绍抱着胳膊笑看着她,那目光将她内心看得透彻,慢慢说:“你可以试着彻底的忘记刹叶这个人,全当为我做事,我可以予你金银财帛,甚至可以帮你脱离戴罪之身,阿毛,我可以让你变成真正元桃,如此一来,你不就再没有任何烦恼了吗?”
李绍一早就看破了她,那双眼在幽黯火光下有摄人心魄的能力,唇角含笑说:“你想要不就是这些吗?金钱,安稳,身份,我说得不对吗?我并没有将你看做普通奴婢,否则我也不必教你读书识字,明德知礼,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这些于你来说遥不可及之事,于我而言却易如反掌。”
李绍看着她的眼睛,朦胧光线下似含着几分真诚:“元桃,留在我身,假以时日,你想要的这一切我都会给你。”
这些固然是她求之而不得的,既有人能够奉上,她自没必要拒绝,脱口而出道:“我当然愿意,可是……”她垂下眼帘,手指攥着裙摆,轻启朱唇道:“可是,奴婢是阿毛,杀过人的阿毛,按唐律犯下的是死罪。”
她问道:“忠王,您知道怎样能忘记吗?”
莫名其妙,李绍被问得怔住了。
元桃只是追问他:“您告诉我,怎样能忘记呢,忘记过去,忘记我曾经是阿毛,忘记并州城里的人吃人,忘记吐蕃王子宅里的血腥残忍……”
她不知道,她才十四五岁,过往就已经压得她喘息不得。
……
“那你现在还会做噩梦吗?”
……
她想起刹叶曾经问她的这句话,她多么想恸哭一场,可她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语气平静的说:“我梦里都是那夜的大火和烧红的天,是那个男人死死掐住我的脖子,是我将匕首捅进他的肚子里,我怕血,可是梦里我的身上都是血,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她看着李绍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