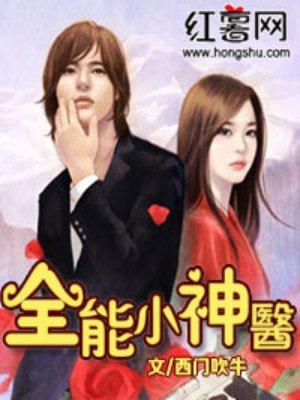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双玉记溯痕 > 第6章(第2页)
第6章(第2页)
于是,几十年的光阴,就在互相置气里过去了。
他最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我可不想学我父亲,将自己弄得那么狼狈。
于是赵景铄会冷着脸说,人家几千年道行,你有他几分本事,尽会大言不惭。
不欢而散。
可是,这气性大的皇帝,自知死期将至,忙着交接皇权,忙着替太子铺路,还要忙着在自己的陵墓里给他这么个半人半妖的没本事的东西布置一个一个的房间,里面汇聚着天下他能找到的所有珍宝,光彩夺目地盼着他来看一看。他将这一个个仓房摆出他能想到的最妥帖的模样,放着他这些年配过的剑,戴过的冠,穿过的甲,常歪在上面的梨花榻和替换的长靴与软鞋。
有满满一屋子的碎银,和足够他再穿百年的衣。
所有的一切,都正对着中间那具寂寥棺木。
它在那孤零零的寒酸墓室里躺着。
仿佛在说,你来看看我罢。
第七章
赵景铄死在一个冬天里。
冬天很冷,冬天年年都很冷。
这年的冬天,又冷雪又大,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盖下来,遮了天与地。
接着就是不出意外的,民居被大雪压塌,压死了人,街边冻死了乞儿和老人。
燃着许多炭盆的皇宫里,也死了人。
临死前的赵景铄面色红润,目光熠熠,连皱纹都仿佛少了许多。
但是沈珏知道,这人要死了。
死亡是这个世上最寻常的事,蜉蝣朝生暮死,昆虫一季而亡,人类也在生生死死,从来没什么大不了。
这一天,大雪皑皑,死了许多普通人,也死了天子。
苍老而年迈的天子,穿着宫里绣娘们赶工的衮服,从里衣到外袍一件又一件,层层叠叠的织布绣花裹紧了他,也撑起了他,让他坐在那里,看起来没那么削瘦。
他坐在寝宫的椅子上,死后的服饰已经穿好,头发也梳理整齐,只是冕冠太重,让太监先放下。
沈珏站在他面前,低头看他认真地摩挲袖口纹路,抚平衣襟。竟笑了笑:“你是怕死后他们装扮不好你么?”
赵景铄也笑了,连朕都不再自称,笑着道:“我只对自己放心。”
“我看着呢,对我也不放心?”沈珏问他。
可是赵景铄没有回答。他只是抬起头来,微微歪过脸,用浑浊的双眼,把这狼妖的眉眼细细打量——浓黑的眉,明亮的眼,英挺的鼻,薄情的唇,多情的笑涡。
这张脸他看了几十年,往后看不到了。
赵景铄看了他很久,没有回答。似乎有什么从他眼底过去了,微微一道水光掠过,快的仿若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
他说:“沈珏。”
沈珏说:“在呢。”
他说:“你跪下来。”
沈珏没有动。
赵景铄很快地微笑了一下,语气堪称轻软:“跪下吧。”
沈珏也歪了歪头,看着他的神情,粲然一笑后退三步,撩开袍摆,双膝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