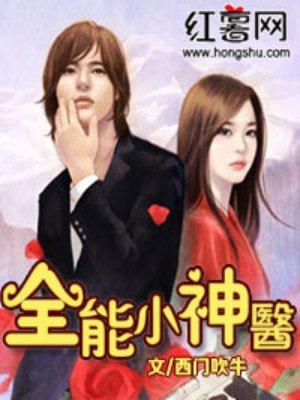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双玉记为什么有两个版本 > 第71章(第3页)
第71章(第3页)
于是伊珏收回视线,笑了一声:“看来你过得还成。”
在山门前哭嚎的小娃娃已经活了很多年,亦送走了很多亲与友,陪在身畔的只有一把殉了炉的剑师兄。
好在他还有个能拜年讨礼的祖宗,在开年的头一天里,唤起了他很多年未听过的乳名。
人是个奇怪的物种,似乎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位长辈在,就有了莫名地安心——即使这个长辈现在成了个不靠谱的小崽子。
沈杞说自己过的还行,现在好歹混了个掌门人,有了师兄和弟子,既没有半路改道变成秃驴,也未曾觉得活不下去想死一死——他好好一个人,偏长了个不嘲讽就活不下去的嘴。
也不知道当年那个总是抱着他的腿甜甜喊着“老祖宗”的小孩儿,怎么就成了这样。
叮铃哐当的杂音突兀响起,打断了迟来的祖孙叙旧,火盆前一大一小闻声同时回过头:
身着吏衣的两道身影站在老梅树下,手上抛着金灿灿的元宝——盆子里的纸元宝烧成了灰,他们脚边的元宝则越堆越多,金灿灿一座元宝山从无到有,堆了有半人高。
个子高的那个人攥着元宝一下有一下无地抛来掷去,有些接住了,有些没接住,没接住的金元宝滚下元宝山,一路发出叮当脆响。
——祭祖祭祖,谁也没想到会真的将土里的祖宗祭来。
两个不成器的小辈脸上一个比一个呆滞,对上梅树下元宝堆后的视线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像是不大想活了,干脆憋死算了。
苏栗抢着往前一扑,魂体都险些从剑身里飘了出来,往地上一戳,邦邦响地磕了头,还不忘大声唱起嗓子给两个傻子提醒:“给祖宗们拜年,祖宗们新年吉祥!”
“祖宗们”笑眯眯地看着这把机灵的剑,抓了一把九幽阴气凝出的珠子塞进了剑身里:“乖。”
雪亮剑身里的魂体冷不丁塞了一把阴气,魂体噌地从剑身里飘了出来,飘飘渺渺的魂身在空中凝实落了地,数不清自己多少年未脚踏实地的少年在地上蹦了几下,一骨碌又跪下去给祖宗们磕了头:“多谢祖宗赏!”
说完他跳将起来,一爪拎起自家的掌门师弟,丢在祖宗们面前摁着其脑袋邦邦响地磕头:“发什么呆,快磕头。”
沈杞被摁着后脑勺磕了两个头,第三个终于摆脱了师兄的魔掌,自己默默地磕下去,磕完没讨赏,往起一跳,三步做两步窜到发呆的伊珏跟前,单手拎起大红团子往两位祖宗脚前一丢:“快磕,该您了。”
——好一个孝子贤孙。
——好一个大孝子葱生。
被丢在地上的伊珏打了个滚醒过神,摆手示意他们等等,甩着小短腿跑去抱着自己的蒲团又跑回来,掏出一把香点燃,举着香扑腾往蒲团上一跪,奶声奶气地喊:“请祖宗们受香,给祖宗拜年,祖宗们新年吉祥!”
说完便举着香,脑壳往地上一砸,这回没手帮忙撑地,险险地呲溜出去,呲溜了半截用脸在地上撑着又险险地直起来。
呲溜了三个来回,石头精红了脑门,脏了脸颊,手上的香火化成灰。
伊珏站起身拍手,小小的爪子捏着大大的手帕给自己擦脸,擦完仰头望着面前的两位祖宗,他未说话,便有冰凉的手自上而下地落下来,盖住了他的脑门,森森寒意比积雪的山巅还要冷,没有一丝暖,是连七窍未通的石头精都承受不住的阴和凉。
他顺着阴冷的力道缓缓低下头,茫茫地看着脚,攥紧了手中脏掉的绢帛。
脑袋上的手掌摩挲片刻便离开,掌心的主人笑话他:“听说你如今不随我姓,是入赘了旁人家还是自立门户了?”
石头精掐着指尖没抬头,慢吞吞道:“没入赘,也没自立门户。”
他鼓鼓腮帮子:“我如今姓伊,”又将声音放的极低地狡辩:
“算是给父亲留个后?”
头顶上传来一道鼻音,拉的长长地“嗯”了一声,沉沉的嗓子轻飘飘地掠过:“那你可真是孝顺的好大儿。”
石头精被嘲出三分羞愤,刚要抬头,又是一张大掌自上而下地落下,比先前那只手宽大些,将他脑壳盖的严严实实,很是用力地往下摁,语气斯条慢理地:
“那你老子就在这里等着,等你带一串姓伊的小崽子来上坟,好不好呀?”
将将要被摁进土里的石头精抻长脖子划着胳膊继续狡辩:“那认养的算不算?您坟边那棵梅树虽然没长脑子,但等它化形了脑子估计能长齐全,它一定特别孝顺,跟您姓,让它每天都给您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