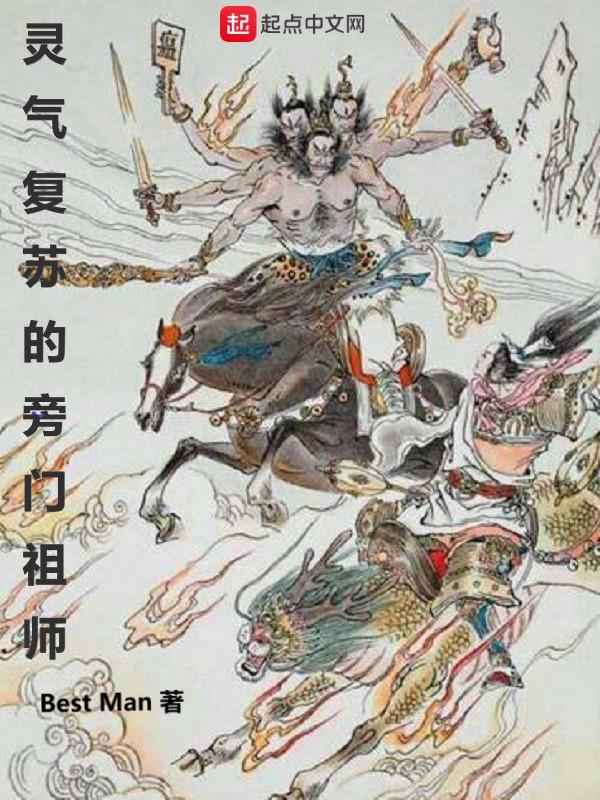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南山客户交互平台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白瞎你这一双眼,谁说我想喝的?”桓秋宁冷哼一声,他把粥推到一边,“我是想看看粥里有没有毒,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十三趴在窗台上凝视着他,“那你看出来了吗?”
“你是不是欠削?”桓秋宁拍了下桌子,“你当我是什么人,药神谷的千年老龟?看一眼就能知道这里头有么有毒?”
“……那你看什么。”十三撇了撇嘴,继续道:“十一哥,你这消息不够灵通啊。现在上京内传的沸沸扬扬的,说太医院去了一位神医,半柱香的时间就把陆决治死了,还说什么五种仙药,连伤鹤淮都出来了。”
屋里头飞出了一个茶杯,十三稳稳接住,一饮而尽。他乐呵呵地说:“还是温乎的呢。”
“上头让你查的人,你查的怎么样了。”桓秋宁转着手中的茶杯问。
“苦菊,一枚弃棋。她的身世没查出什么东西,进宫的路子也很干净。但是,咱们铜鸟堂的人如果只能查出这么点东西,早就死了一万回了。”十三靠在窗台,叼着一根草,“她那死去的祖母是章管家托人埋的,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苦菊没能尽孝,死后苦菊想让她入土为安,所以她去了常安当铺。她当了一件宫里的东西,当铺老板不是傻子,他不可能要钱不要命,所以他找了照府的章管家,也就是这家当铺真正的当家人。”
“她从宫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桓秋宁问。
“一枚玉佩。”十三摇了摇腰间的钱袋子,“不是普通的玉佩,是双云郡的空山玉。玉佩有半个巴掌大,镂空的,里面有两枚永安钱。”
“……永安钱。”桓秋宁打了个响指,他轻笑道:“贼鼠一窝。”
十三挠了挠头问:“谁是贼,谁是鼠?”
“这件事已然明了,苦菊是照宴龛的人,照杜两氏对立,朝中已经出现了踩着他们往上爬的势力。”桓秋宁慢条斯理地道,“搅局者开始布局了。”
“十一哥,能说明白点吗?”十三听得一头雾水,他腆着脸笑了笑,见桓秋宁懒得解释,只好自己哄自己,闷声道,“行嘞,那我自己捋捋。”
十三思索道:“苦菊是照宴龛的人,毒是她下的。羽林军里头大部分都是身世清白的子弟,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搅浑水,嫁祸给杜卫,搓一搓他在军中的气势。十一哥,我说的对吧?”
他以为桓秋宁会夸他一句“孺子可教也”,结果桓秋宁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么想下去,越想越偏。”
桓秋宁的眸色愈发深沉,低声道:“苦菊是照宴龛的人,他走这一步棋,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照芙晴入昭玄寺。一方面是为了撤出安插在稷安帝身边的眼,另一方面是因为照芙晴出了宫,他就能彻底地放开手,去布下一个局。我有预感,他要布的这盘局,会赌上他的一切。”
他单手撑腮,不疾不徐:“而且你忽略了一个人——狄春香。棋子落盘,步步为营,必然会有它存在的意义。狄氏是太祖时期的显赫贵族,这些年在朝中势弱,他们想要站起来,就必须先傍上靠山。杜卫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武将,他们需要谋士,狄氏愿意做他们的谋士,两氏距离一拍即合就差一步——诚心。杜卫要看到狄氏的诚心,才能决定这个盟要不要结。”
“狄春香就是那个‘诚心’?”十三又问,“可是我听说狄春香和陆决可是老相好,她能谋杀自己的有情人?这不可能吧。”
桓秋宁的十指在枣木桌上敲了敲,冰着脸,满不在乎地道:“感情这种东西,在利益面前,就是狗屁,没有人会一直对你真情实意。在你风光的时候冲你摇摇尾巴,等你跌落深渊之后,他们还会倒踩一脚,而且比别人踩得更狠。”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也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十三耸了耸肩,他脑子一转,突然问了一句,“十一哥,那你跟照山白这算什么,千里姻缘一线牵?他是断袖,你也不直啊。”
“那是传言。”桓秋宁平静地注视着他,他越是平静,十三就越是害怕。于是他灵光一现,想起了之前在大门口听见的一句话,拍了拍手,笑道:“你们是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
“……”桓秋宁的五官六亲不认,恨不得立马分家。
“你是王八,他是绿豆。”十三还没意识到骤然吹来的冷风,一边笑一边说,自顾自地笑道,“绝了!”
桓秋宁摆了摆手让他过去,十三不敢,缩在窗后瑟瑟发抖。
桓秋宁忍了,他跟照山白的关系三两句话说不清楚,干脆不提,免得越抹越黑。
桓秋宁心平气和地道:“去查永安钱。狄春香是杜卫的人,她故意在房内放了永安钱,又在诏狱全招了。柳夜明拿此大做文章,绝对不只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想通过永安钱引出点什么……”
“陆决之死,狄氏,永安钱……难道他们引出永安钱是为了让柳夜明查照宴龛?”桓秋宁思索了一会,思索道,“永恩三年照府的账肯定还有问题,我们要先人一步。”
十三听得一头雾水,脑瓜子嗡嗡的,他腆着脸,拘谨地问:“十一哥,咱们做死士的,真的有必要想这么多吗?”
“死士?”桓秋宁笑着把玩着了手中的瓷杯,似笑非笑,挑眉道:“从狼群中踩着累累白骨爬出来的人,这辈子不可能再把生死交在别人手里。我站在上京的城墙上,只能看到孤魂野鬼,他们告诉我,没有什么比活着更有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