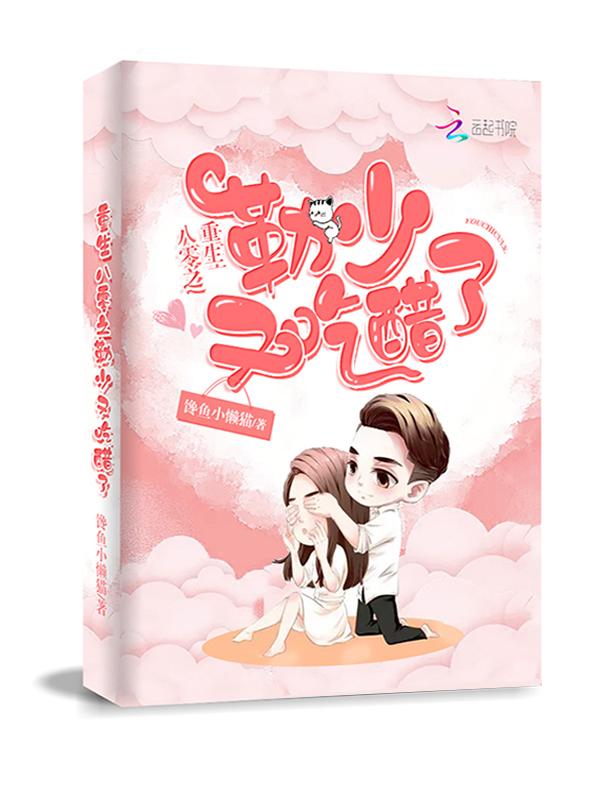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珠玉为心以奉君打一数字 > 3040(第13页)
3040(第13页)
他这句话轻不可闻,随着穿帘而过的晚风一齐被碾没在辘辘的车辙声中,檀禾并没有听见。
谢清砚初时为她的一窍不通而头疼,不过在循循善诱逗弄中,倒得了另一番趣味,除了他也同样备受折磨外。
在檀禾将要啃完第二只蝎子时,谢清砚很上道的递去海东青。
在行宫这些日,檀禾已然习惯他的照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时常让她有种自己才是在养病的错觉。
她叹了口气,明知不能再这般懒散下去,可身体已经下意识蹭过去,就着他的手咬上鹰翼。
原本精致潋滟的眉目间攀上一丝怅然,方才还满脸欣喜雀跃的。
谢清砚看在眼底,忽然抬起手,将她一绺垂落的发丝拢在耳后,长指自然而然地滑过耳廓,顺势勾了勾小巧的耳垂。
权当是收取的报酬。
谢清砚很有耐心问:“叹气做甚?”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不疾不徐,听上去静默而温柔。
周遭昏黄瞑暗,几案上的灯盏亮光,忽明忽暗映照出轮廓深刻的面庞,清晰可见眸底如深流过渊。
檀禾仰脸看他,没有如实相告,而是闷闷又叹:“腮帮子嚼得累。”
这样下去不行,否则等她日后回了望月山,会非常不适应没有殿下的……檀禾绞尽脑汁想到一个词——
侍奉?
……
时隔半个多月再回到东宫,谢清砚开始照常朝参上值,又因公务繁忙,自回去后,便未再踏足东宫。
如今朝野上下一片翻天覆地的震动。
监察御史弹劾大司马董淳峰贪腐,事后清查发现确有其事,他仅督师齐鲁这几年所贪的军饷,就达十五万两,更是常年虚报兵额,贪吞空额。
如今董淳峰阖府上下一并被收押入狱候审。
金銮殿上,仁宣帝为此盛怒了许多天。
虽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但当今储君的身体状况满朝文武都清楚,说句大逆不道的话,皇上又子嗣不丰,难保最后皇位上稳坐不是怀王。
董淳峰背后是盘根错节的朋党势力关系网,定然是要牵扯到怀王。
若是彻查下去,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大事落手里,成与否,兴许日后都得被报复掉脑袋。
是顾,除了查出贪冒军饷,再往下追查军饷流向何处却毫无进展。
这日早朝,仁宣帝下了口谕,命太子及诸位大臣彻查董淳峰一案。
谢清砚眼底闪过淡淡嘲讽冷笑,早料到仁宣帝会将这案子推到他身上。
他比谁都清楚,仁宣帝惯会隐身幕后借刀杀人,既想要坐山观虎斗,有想要得利,着实是贪。
不过倒是正中了谢清砚下怀,仁宣帝既然钝刀割肉般凌迟了他二十多年,谢清砚不可能会放过他,必然要回之一份大礼。
巳时初,耀眼的日光穿透窗格,融入这方阔大殿,却照不透谢清砚满身的凛然寒意。
散朝之际,内侍急忙躬身上前传话:“请太子殿下留步,皇上在御书房召见殿下。”
盘龙鎏金熏炉中一缕龙涎香缈缈弥散,仁宣帝透过缭绕的烟雾,双目落在阶下巍然屹立的青年身上,墨发玉冠,俊朗肃沉的面容呈现出几分苍白。
仁宣帝眯了眯眼,嘴唇翕动:“董淳峰一案牵扯甚广,你身有沉疴,也切莫劳累伤身。”
谢清砚锋芒深敛,漠然道:“儿臣多谢父皇。”
一如往常的回答,仁宣帝继续道:“因着董
家,朕这些时日被扰得身体抱恙,正好李言钦也在此,让他顺道给你请个脉瞧瞧。”
闻言,谢清砚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了声,撩袍坐在椅上神情莫辨。
垂首候着的李言钦见状移步上前,深揖一礼,于一侧跪下:“请殿下将手伸出,臣为殿下望诊。”
在对上太子冷然戾沉的漆眸,李言钦瞬间额上冒冷汗,垂下眼。
李言钦小心翼翼切脉,面上凝重。
阶上仁宣帝斜倚龙榻,一目不错地看着底下,神色莫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