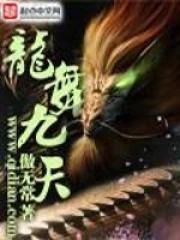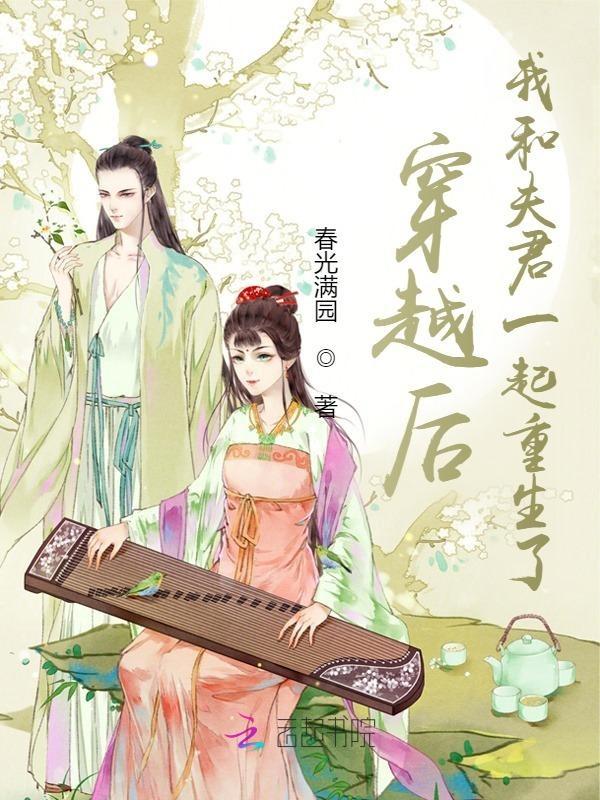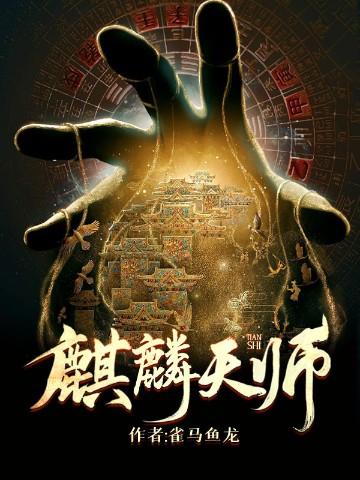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女侠的风格 > 夜话(第1页)
夜话(第1页)
顾小枫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模样有用的,大概得追溯到三五岁,想吃蜜饯时,只要在母亲面前哼咛两声,母亲就会心软。
再大点的时候,不管去了世门宗亲的哪家,都会引得别人,一边嗟叹好俊一边要在他脸上掐一手。
要是犯错了,口气一软姿态一低,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甚至还会有人主动帮他找借口想理由,就算是最见不得他这副姿态的父亲,也回回都被他堵的说不出狠话,更不会有像其他家顽皮少年,动辄被挂在树上打的挫折教育。
顾小枫分不清什么时候这些行为变味的,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没人再把他当孩子温视了。还是因为母亲去世后他没了最柔软的靠山,所以那些偏见与轻贱便张牙舞爪地滋长了出来。
或者单纯就是环境变了,毕竟年少时,上京人开赏花会比的是吟诗作对,而现在每年赏花的“花”都变成了名伶和男倌,真正的花却成了无人在意可有可无的陪衬,诗当然也是要作的,只是再难见清朗高洁之作,多是靡靡轻薄之音。
而顾小枫那点作态也从主动变为被动,也早就没有过去邀宠耍滑后的得意,更多是九死一生的侥幸,他幼时会庆幸自己长了张讨巧的脸,现在却偶尔会感叹要是自己平庸些就好了。
甚至在得知父亲叛国的消息时,当那种担心与错乱的情绪平复后,心中升起一阵恐惧,那些过去委婉压抑的审视怕是要没有避讳和芥蒂。
而面对祝洵,顾小枫难得有不需要惺惺作态的时刻,可以不顾忌身份、环境、相貌等一切身外之物,来讨论抱负与理想。
更微妙的是,他久违的有了一种类似于对着母亲撒娇,对着父亲耍赖的无忌感,这种舒服妥帖的感觉来源于完全的安全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安之若素。
他可以对着孟钰说他的啰嗦像娘,却无法对着祝洵说出任何,这种感觉太私人化,有点禁忌又有点害怕,怕一说出来就什么就没有了。
顾小枫从小没有骨肉兄弟,也没有相熟的同龄友人,祝洵算得上第一个,再加上出现的时机又那么特殊又戏剧,不免心中嗟叹大概这就是难得的缘分。
于是虽然相识不久,也禁不住回味一起经历的种种:“阿洵我觉得你有点变化,刚见你时你从天而降,对着陈爷那些人直接挥剑夺命,还有我要被刘海他们证身时你也差点就拔出剑来……但是现在你好像……其实我刚才还担心你不愿被杖刑要驳徐大人呢。”
祝洵沉默了一会说道:“其实在闽州时,没遇到过这么多复杂的情况,那会儿跟着师傅,有水匪就下海剿匪,有山贼就上山杀贼,清干净了,闽州就能安居乐业好久,所以我习惯了去直接解决引发问题的人,一劳永逸。”
“但出了闽州,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总觉得找不到引发问题的源头,杀掉一个十个哪怕一百个也无法安生,甚至有助长杀虐,于事无补的无力感。以前我以为做侠客铲除不平靠一把剑就够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痴人说梦。”
“就像你,也算是名门之后,受尽庇佑,家里刚受难就有人敢……更别说比你孱弱势微的芸芸,我现在是彻底理解,李盈姐妹为什么要扮男装了。”
“之前和你说想让天下皆变闽州,这样的抱负听起来有些光大,也有些圂囵,说得更具体一些,我想让所有的积弱之辈,生无所惧,行有所长。我刚才一直在想靠我一人怎样才能实现,甚至脑子里冒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也许我像徐立那样,就可以……”
顾小枫一直静静听着,他其实有些惋惜于祝洵无法再如从前那般天真,但听到她说想像徐立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我记得之前你和我说过,徐大人不可靠……”
“我现在也觉得他不可靠,但他有他的法子,我有我的坚持,要是能合二为一,算得上是各补所长。”
顾小枫沉吟片刻:“其实,你可能对徐大人有偏见,他这样的位置难免有他的得失观念……而且拿我作饵也不是他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帮我查清父亲叛国的事情。”
祝洵听完一个激灵:“你们聊过……还是说他认出你?”
顾小枫摇摇头:“他应该是初到上京,也不浸染烟火柳巷,应是完全不认得我,他也没对我讲过父亲的事,只是他出身武德司,这次北上主要就是为了查御北关失守的事宜。”
“而且从他对安南军以及江小将军的态度来看,他算得上难得的清流,我很难描绘这种感觉,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入身行伍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也不是为了拥兵自重,而是他想要南越海晏河清四海平定。”
“如此来看,他也一定会查清父亲在御北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和你说,你可能会觉得可笑,就当我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自我安慰吧。”
祝洵听得明白这话中含义,徐立有权有谋有勉强算得上正义的不偏颇,是有能力且意愿查清御北关之事的不二之选,她也认可这点。
“其实我偶尔在想,既然这天下不同闽州,我也不应该拿闽州的度量要求人,毕竟连我在中原才待了这几日,就会有想改变的想法。也许,徐立这样的人,在闽州长大,会长成和我相似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