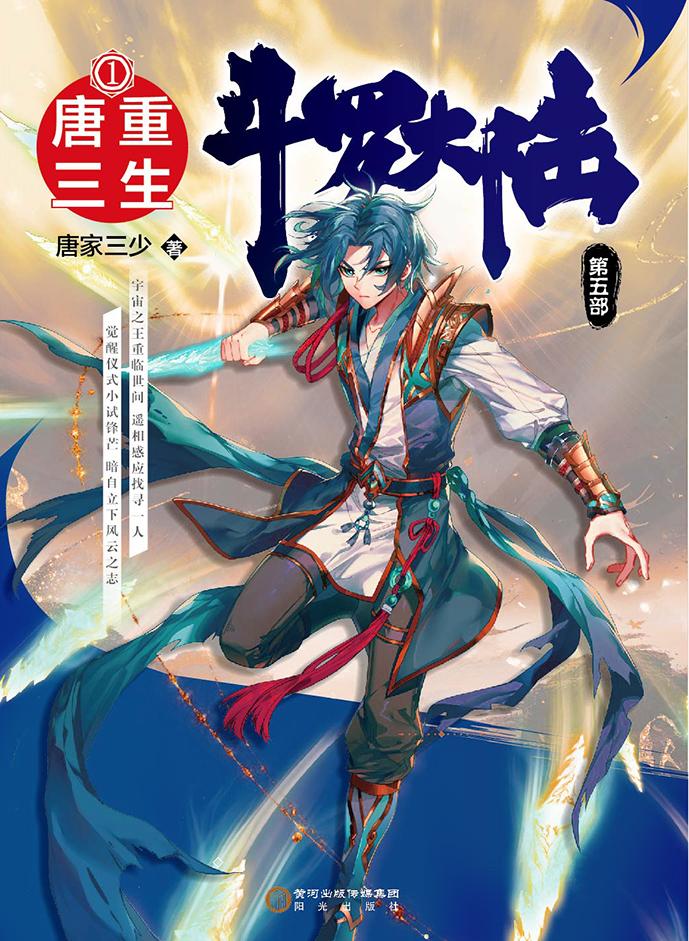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仅此一次什么意思 > 26杀死汉武帝1(第2页)
26杀死汉武帝1(第2页)
以前李茉就很奇怪,以往的“古代农女”剧本里,总有一个封建、偏心、碎嘴的老太太,针对女主的伯母、婶子、大姑、小姑,这家却没有,繁重的农活压得每个人都很沉默。
大母去世了,家里最年长的长辈是大父,大伯和伯娘都很沉默,生的两个儿子也不像印象中的小孩儿那么活泼,偶尔农闲时他们在院子里呼啸往来,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时候一向沉默的大父会发出“伽伽”的驱赶声,仿佛在放牛。
最神秘的是西屋,一直有声音,一直没有人出现,去看也不会被开门放进去。直到今日,李茉才知道一直响动的屋子里住的居然是自己的姑姑,家里人却没提过,这太奇怪了。
李茉从院子里又逛回织室,大父、大伯家的房间都上锁了,她推不开。
天色渐渐变暗,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李茉闻声而动,赶忙出门招呼:“大父、大伯、伯娘、阿父、阿母、大兄、二兄……”
两个堂哥对李茉笑笑,大父却皱眉,挥挥手,“回西屋去!”
李茉今天第三次被父亲拦腰提溜回西屋,过了一会儿,母亲端来两碗稠厚的粟米粥和一碟子腌菜。“她姑,孩子就托给你了。”
许久,织机停下,女人起身。
李茉吓得倒退一步,这个女人的后脖颈上肿着大大的一块肉包,坐下不显,站起来仿佛一个肉瘤,不知是驼背还是什么病症,像富贵包的严重版。她一直低头坐着织布,等站起来,李茉才发现她脖子不能伸直。
难道这就是家里人把她关起来织布的原因?古代好像真的对病症很迷信啊。
织布女慢慢走过来,冰凉的手指触了触李茉的脸颊,李茉看不懂她的眼神,只听到她沙哑干渴的嗓音:“也是可怜……叫我姑姑。”
姑姑夹着李茉的胳肢窝,把她放在门口方桌旁的矮脚板凳上,端起粥碗,唏哩呼噜灌下半碗粥,筷子在粥碗搅动,只起一个降温作用。
把喝得只剩半碗的粥递给李茉,姑姑端起另一碗粥,就着腌菜,慢慢吃起来。
李茉没哭,也没嫌弃,她已经知道农家粮食珍贵,李茉双手捧着粥碗,放到桌边,站起来,手扶着碗慢慢喝。她太小了,无法长时间端着粥碗。而打翻粥碗、甚至打烂碗的后果,看看之前大堂哥被抽红肿的屁股就知道了。
物质极度缺乏的时候,东西比人金贵。
姑姑看她小小的人却聪明得知道自理,心里有瞬间的高兴,可想到这孩子以后会走上自己的老路,又觉得聪明不是什么好事。
一日两餐,以往,姑姑每餐只有一碗稠粥,今日多出的这半碗,就是家里默认给自己养孩子的报酬。姑姑再看一眼能自己吃饭的侄女儿,低头吃自己的。
吃完,姑姑把两个碗一个碟子放在门口,抱着李茉给她把尿,羞得李茉脸颊通红。
回到织室,姑姑拿一根破布拼接的长布条栓住李茉的腰,栓狗一样,把她栓在织机旁。
咔、咔、咔,规律、枯燥的织布声又响起来。
“姑姑,我不乱跑,不用栓。”李茉小声抗议。
姑姑没说话,要不是听到过她开口,李茉差点儿以为她是哑巴。等天色彻底暗得看不见了,姑姑也停下织布,去厨房舀了热水来洗漱。
“农忙呢!柴可紧,天不亮我家阿郎就去山上砍柴,大牛、二牛都不得歇,天天屋里坐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怎生还用这么多热水?”伯娘站在厨房门口,脸上挂满寒霜。
姑姑回头看她一眼,没说话,继续往前走,伯娘不依不饶追上来,“说你呢!哑巴了!”
姑姑被她拉得趔趄,泼了热水,高声回道:“布脏了,跌价。不让洗,不织了。”
她说的句子很短,每个短句之间有明显的停顿,仿佛在说之前,已经想好的每个字,又仿佛长久不说话,功能退化,只能慢慢表达。
伯娘一愣,立刻哭嚎起来:“苍天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大郎!大郎……”
一嗓子没招来大伯,倒是正房的房门嘭的一声弹到墙上,大父从门口出来,月亮照出他的身形轮廓。他不用疾言厉色,只露面,就让人感到无声的压迫。伯娘不敢说话,姑姑也不梗着脖子用眼刀剐人。
“歇了,明天收麦呢!”大父如此吩咐,一场口角消弭于无形。
姑姑又去厨房的陶锅里舀热水,端进西屋,先自己洗了,又给李茉擦。随后,把冷掉的水,泼到墙角菜地里,回屋上锁,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李茉躺在窄床上,身体挨着姑姑,听到东边传来大伯、伯娘偶尔飙高的调子,听到隔壁父母悉悉索索的声响,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凭什么?我自个儿丫头不能养,老三家的就行,我可是给你们老李家生了两个金孙!”黑夜里,伯娘的抱怨,并不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