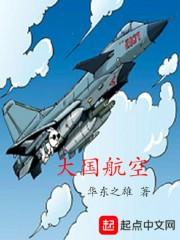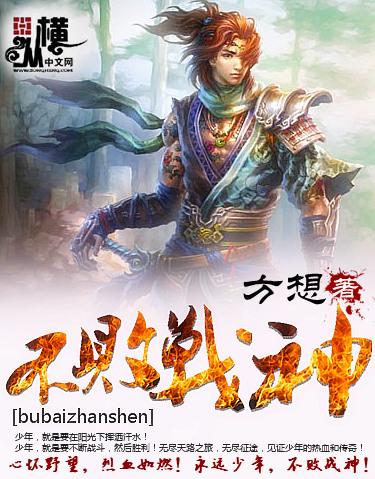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靠种田养媳妇[穿越 > 11发粮(第2页)
11发粮(第2页)
“上个月阿坤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呢,等这次回来,手边有了银子,就带着嫂子和娃儿分出来单过,还说让我帮着盖房子呢,可惜……唉……”
曲花间听着佃户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李坤的妻子余三却无动于衷,仿佛他们说的不是自己,她睁着空洞的双眼将儿子圈进怀中,眼泪如未断线的珍珠,噼啪直掉。
“我说了,这钱是补贴给父母妻儿的,所以分为四分,你们四人各拿一份。”曲花间冷着脸,挥手让护院将李老汉两口子还没来得及拿走的银子数出一半来。
那两口子本来听到有人在东家面前碎嘴子便开始对着那人破口大骂,但对上曲家的护院,胆子比自己大儿媳妇还小,根本不敢反抗。
甚至在曲宝沉着脸呵斥一声后,连骂声都收敛了回去,灰溜溜的拿着属于自己那份钱粮准备离开。
“等等!”曲花间叫住李老汉,从怀里掏出一叠写满字的宣纸,“拿了补偿款的,未免以后有什么纠纷牵扯不清,要在收据上按个手印,才能走。”
说完,曲花间将早就拟好的收据让曲宝大声念给众人听。
在李老汉和余三分别在一张收据上按了手印后,曲花间又看向余三。
余三本来因为丈夫的离世而生出的怨恨消散了些,她紧紧抱住儿子沉默不语。
二十五两银子和一百五十斤粮食足以让她们孤儿寡母衣食无忧好几年了,等孩子大些,有了生存的能力,日子总会好过起来的,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家今年准备在西面的平顶坡开荒出来种些从南方买回来的粮食,现在正好缺人手,你要来吗?包吃住。”
曲花间温润的声线传入余三的耳朵里,她猛然抬头,眼睛通红。
她一个寡妇,带着个儿子,想要再嫁太困难了,何况她也不想改嫁,可若回了李家,即便东家做主分了钱粮给她,她又能保得住吗?
倒不如去给东家干活,哪怕苦点累点,至少能将自己和丈夫的血脉好好养大。
“我愿意!”余三嗫嚅着唇,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我愿意!谢谢东家!”
“好,曲宝,你给余娘子登记一下,其他有人愿意的,也可以找曲宝登记,具体的报酬等过几日再通知,现在先继续发补偿款。”
李家的事情告一段落,刘家的补偿款发得比较顺利。
刘家人丁单薄,又都是老实巴交的,刘平的父亲沉默着领了钱粮,将银两交到呜咽着抹眼泪的老伴手里,便在大儿子的搀扶下缓缓走开了。
剩下的,便是重伤员的补偿,受了重伤爬不起来的船员一共九个人,其中有四个是曲家护院,另外五个从佃农里雇来的,这些人都送到了曲府,请了大夫回去医治。
曲花间给这五家人都发了三百斤粮食和二两银子,又承诺等这几个人伤好之后再给本人补偿十两银子,若是不治身亡的,也给家人补齐五十两。
这几家人都没什么意见,老老实实领了钱粮退开。
剩下的,便是轻伤和没受伤的船员,这些人的钱粮都是本人来领的,没受伤的二两银子一百斤粮食,这是原本便说好了。
受了伤的,按受伤程度给了一到五两的汤药费。
像李家嫂子这样贪心不足的人到底是少数,其他人对曲花间这样安排几乎是感恩戴德。
要知道,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工伤的说法,除非是做工时死在工地上,家里人去闹上一闹,能得个几两碎银子都是好的。
绝大多数人在给人做工时伤了残了,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能保住这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扛不住的,管事才不会管你是不是做工时受的伤,直接将人丢出去了事。
对比起来,曲花间出手阔绰得简直像是活菩萨转世。
发完船员们的报酬和补偿款,曲花间又将佃户们的当家人召集起来开了个小会。
曲家的千亩良田分四个庄子,每个庄子上有一个管事,负责田地和佃农们的大小杂事。
说是管事,其实也就是佃农里选出来的稍微精明能干些又识得几个大字的人。
此时管事们低眉顺目逐一汇报着各自庄子上的事宜,时值三月,春耕在即,佃农们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粮种都已育上苗,再有十天左右便可以插秧。
“各家秧苗情况你们可都清楚?够不够数量?”
邻河庄的杨管事是四人中最会来事的一个,平日里和主家接触最多的便是他,此时也是他回答曲花间的问话:“庄稼人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粮种给吃了的,可今年实在艰难,估计全部种下去,能有一半空田。”
“一半?”曲花间蹙眉,却也没说什么,毕竟佃农们若不是凑了那么多粮食给曲家交税,也不至于那么艰难。
“南方的稻种比我们这的品种好,但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北方的环境,我买了一万五千斤稻种回来,先按每亩空田发五斤下去,让他们抢时间种下去试试。”
“另外再按老人一百斤,年轻人一百五十斤,孩子八十斤的标准给每家发粮食,算是还去年大伙儿凑粮食给我们交税的人情,这些粮食,只要省着点吃,应该够撑到秋收了。”
交代完各项事宜,曲花间坐上将伤员运回去又折返回来接他的马车,赶在城门关上之前进了城。
天色渐晚,曲宝点亮了挂在车檐上的油纸灯笼,纸灯笼散发出昏暗的灯光,照亮了曲花间略带青黑的眼圈。
曲花间透过车窗观察着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看着熟悉的店铺招牌,总算有了点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