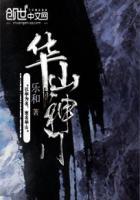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炮灰等级 > 书斋听训(第2页)
书斋听训(第2页)
楚绢心中一凛,暗道:这便开始考校学问了?
她不敢怠慢,垂眸思索片刻,先上前一步,恭敬地行了一礼,起身后道:“回先生话,学生以为:器者,形也,是具体的器物,有其固定的功用和形状。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应像器具那样,被外在的形制或世俗的期望所束缚,而应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不拘泥于方圆,不被外物框定。”
她一边说,一边缓步走近案前,伸出纤细的食指,虚点在案上的端砚上。“譬如这砚台,其本是研墨之器,但亦可用来压书镇纸,甚至在紧要关头作为防身的武器。再如这狼毫笔,可用来写小楷,工整细致;亦能挥洒泼墨,画竹石山水,描绘万千气象。
“器尚且如此,更何况人?虽说君子有道,可人若只知固守一隅,便失了生机与变通的可能。所以弟子以为,不拘方圆,方能成大事。”
楚擎峰听罢,抚着胡须,仰头大笑:“好个不拘方圆!自天下尊儒重礼,代代士人皆以守礼持身为君子之道,严谨有余,却也渐渐将礼法变成了束缚自身的绳规,甚至是难以挣脱的枷锁。”
他那爽朗的笑声在书斋中回荡,却在下一刻戛然而止。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楚擎峰的目光沉静下来,带着一丝深沉的忧虑:“可你知道,我为何独独考你这句?”
楚绢心中一动。原著里曾隐晦地提过,楚家曾因过于拘泥于祖宗成法和礼教,而拒绝了当时颇具革新精神的变法派主张。
虽然书中并未明确交代最终的下场,但作者的言语间,却隐隐透露出不认可和惋惜之意。
楚擎峰此刻提及,恐怕不仅仅是在考较她的学问,更是在暗示家族积弊,以及他自身在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艰难抉择与内心的挣扎。
“族长是想说,礼法之外,更要存变通之心?”她试探着接话。
“不错。”楚擎峰缓缓起身,踱到窗前,目光投向窗外,望向后院那株在春风中微微摇曳的老梅,眼神悠远而深邃,“礼法,是约束世人的准绳,维持秩序的基石。可是,一味地守礼,不知变通,也难以在波谲云诡的朝堂漩涡中保全自身,更遑论谋求发展了。
“你父亲先前……唉,便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固执己见,我曾劝过他许多次,可惜……不过,好在他最后还是想通了。”
楚绢心神一凛,没想到会突然听到这等密辛。
这是否是楚擎峰在藉由她,向千里之外的楚怀庭表达接纳和认可?是对父亲改变观念的一种肯定与期许?
楚擎峰转过身看着楚绢,眼含满意之色:“你很好,好得超乎我的想象。我楚家需要的,不是只会背诵女诫、恪守妇德礼教的弱女子,而是身负经世之才,能撑起门楣的大器。”
话落又是暗暗惋惜,此子天资聪颖,若投胎作男儿身,必能成为楚家新一代的翘楚,在他之后,带领整个家族再上一层楼。
而今只是个女儿家,真是可惜,可惜。
在世俗的眼光和家族的传统中,女儿家的才学智慧,终究是难以完全施展,难以真正担起家族的重任。
楚绢的心猛地一沉,随即又涌起一股不甘。她忽然明白了,楚擎峰今日召她来,不仅是考校她的才学,更是试探她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打破楚家的困局,为家族带来新的生机。
“族长教诲的是,绢儿谨记在心。”她突然跪下行一道大礼,额头几乎触碰到冰凉的地面,语气却异常坚定:“绢儿愿学,也愿用所学为家族分忧。纵然身为女子,亦当竭尽所能,不负族长所托,不负楚家血脉!”
楚擎峰定定地盯着她看了半晌,那目光仿佛要将她看穿一般。忽然,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动作中带着一丝长辈的嘉许与亲昵:“绢儿觉得,院子里那株老梅如何?”
楚绢回忆了一下方才透过窗棂看到的景象,诚实答道:“那梅树枝形奇绝,铁骨铮铮,风骨不凡,颇具孤高之气。只是……古语有云,独木难成林,它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看去也有些落寞。”
楚擎峰眼神微动,幽幽闪闪,最终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道:“你去院子里,择一支梅花带回去吧。它是我官拜太子太傅那年亲手所植,算来,已在楚家扎根四十余年了。”
楚绢应声退出书斋,脚步轻快。穿过院门时,正听见身后传来楚擎峰对老管家的吩咐,声音清晰而郑重:“去,把东厢那间空房收拾出来,给楚绢做书房。再把我书房里那些藏书清点一番,仔细挑拣些好的搬过去。”
一阵春风掠过廊下,带着早春花草的芬芳,吹得老槐树簌簌落下几点细碎的淡黄色花苞,轻盈地停驻在楚绢的肩头。
她抬起头,望向后园那株虬枝盘曲的老梅,只见枝桠间仍余星星点点的红蕊,在料峭的春风中悄然绽放,娇艳欲滴。她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里,红梅树下曾发生过多少恨海情天,见证过多少女孩儿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如今,她站在这里,该换一种活法了。
她楚绢今日立誓,终有一日要让女子不必再做笼中雀,亦可以长成翱翔天宇的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