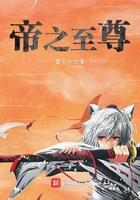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第一个老师 > 第13章 织声(第2页)
第13章 织声(第2页)
琴房门口贴了一张纸条:【请勿打扰?正在录音】
他知道,真正的比赛和日常练习之间差了不止一条水沟。
只有在录音中,他才能听见真正的自己??那些平时弹过就忘、现场却无法挽回的细节。
他也知道,前世的自己就是倒在这些细节里。
《悲怆》奏鸣曲,他弹得近乎克制。
每一个进入、每一次过渡、每一组重音的铺排都像是建筑工地上的梁柱,反复测量后才落下。
不是热情驱动,而是结构判断。
是他从前世一次次失败与崩塌中,反刍出来的判断力。
他听得出,自己在“搭建一件作品”,而不是演奏一个情绪。
演到第二乐章,他明显感觉体力在缓慢下沉,但没有停。
他要知道,在体力边缘、在真实的疲劳状态下,自己的音色还能不能维持。
这不是临时演出,而是提前模拟五年后的华沙。
进入德彪西时,他换了口气,闭了闭眼。
这部分的技术难度不大,但听觉要求极高。
音色像空气一样滑脱、柔软、不可捕捉。
而他对这种声音的敏感,来自另一个人生的积累。
他让自己像个听觉的雕刻工??
每个音该有多少“沉”,多少“浮”;
踏板放在几分之一拍后,才能带出延音的“拖尾”;
他甚至计算过每一段弱奏后,静止几秒最合理。
这些听觉设计,不是少年能轻易做到的。
他清楚,这是他前世唯一带得回来的东西:对声音的感知经验。
这一刻,他不是在演奏旋律,而是在安排空气的密度。
结束时,他没有收尾太快,而是刻意放缓最后一组踏板的松开。
让那组和声像雾一样散开,再慢慢隐没。
江临舟关掉琴盖,收起录音笔,打开门。
走廊昏暗,一盏顶灯闪了一下,又亮起来。风从窗缝吹进来,带着一点洗地水的味道。
他正要下楼,却在转角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陈雨薇。
她倚在窗台边,背着琴谱包,一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脚尖轻点着地砖,不知在等谁,或只是站了一会儿。
听见动静,她偏头看了他一眼。
“试录?”语气平平,是一句确认而非提问。
江临舟“嗯”了一声,没多说。
她点了下头,低头像是想了下,忽然道:“你那组曲子……挺花力气的。”
这句评价不轻不重,也不含褒贬,像是一个练琴人对另一个练琴人的默认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