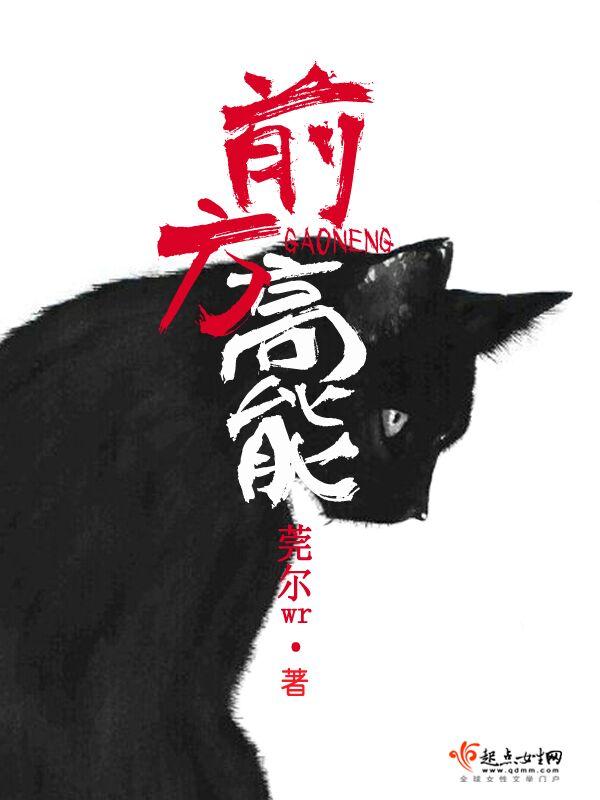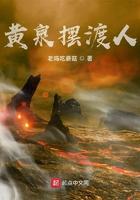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倒爷到世界首富 > 第396章 初探地窖(第2页)
第396章 初探地窖(第2页)
“那时候玉米壳重,带壳交能多算点分量,”赵铁柱解释道,“但他肯定是不好意思全带壳,不然账本上不会特意记‘已筛’——收粮的人知道他实诚,帮他把壳筛了。”
翻到最后一册,账本的封底夹着一张小画,画的是个简易的磨盘,旁边歪歪扭扭画着个小人,手里举着个碗,旁边写着“磨啊磨,磨出白花花”。
“这是孩子画的吧?”周丫指着小人,“跟我画的一样丑。”
老周接过画,摸了摸纸面:“像我家那口子小时候的笔迹,她总爱画磨盘,说长大了要当磨盘匠,让家家户户都有新磨盘。”他眼里闪着光,“后来她真嫁给了我这个修磨盘的,也算遂了愿。”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赵铁柱继续在地窖里翻找,在最里面的角落发现了一个铁皮盒,锁已经锈死了。他撬开盒子,里面没有金银,只有几枚铜钱、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块磨得光滑的鹅卵石。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并肩站在磨盘边,笑得很灿烂。“这是……”赵铁柱把照片递给老周,“您认识吗?”
老周接过照片,手突然抖了一下:“这是我哥和嫂子!他们……他们当年为了护地窖里的粮食,被土匪杀了……”他声音哽咽,“这照片我以为早丢了,没想到在这儿。”
铁皮盒里的鹅卵石上,用红漆写着个“安”字,漆皮已经剥落大半。老周着石头,哽咽道:“这是我哥的石头,他说‘磨盘转,日子安’,总把它带在身上。”
孩子们看着老周难过的样子,都安静下来。周丫把擦干净的“丰”字碗递过去:“周爷爷,用这个碗喝点水吧。”狗蛋也把那张小画递上:“这个,给您。”
老周接过碗和画,抹了把脸,挤出个笑:“好,好,谢谢你们。”
赵铁柱把地窖里的物件一一整理好,账本、陶碗、铁皮盒、照片……摆了满满一磨盘。阳光透过棚顶的缝隙照在这些旧物上,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像把过去的时光都照得透亮。
“这些东西得好好收着,”他对孩子们说,“不是为了记着苦,是为了记着当年的人怎么过日子——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楚,一点一滴都想着别人。”
张大爷找来几个木箱,把物件分门别类装进去:“我看啊,就放在磨香棚的角落里,做个‘老物件角’,谁来了都能看看,讲讲过去的故事。”
老周把照片放进贴身的口袋:“这张我得带走,想他们了就拿出来看看。”他看着赵铁柱,“小赵,谢谢你把这些东西挖出来,不然这些故事,就真的烂在地里了。”
赵铁柱笑着摇头:“是这些老物件自己想出来了,想让孩子们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周丫拿起那个“丰”字碗,往里面装了把新收的小米:“看,现在碗里有新米了。”
狗蛋也学着往陶瓮里放了把玉米粒:“这个也装满。”
地窖被重新封好,石板盖回原位,只是这次没有用灰浆,只简单压着,像给过去的时光留了个透气的缝。磨盘转起来时,发出比往常更轻快的“吱呀”声,仿佛也在跟着念叨那些刚被记起的故事。
赵铁柱看着磨盘上的新粮,又看了看角落里的木箱,忽然觉得,日子就像这磨盘,旧的粮食磨成粉,新的粮食又倒进来,磨着磨着,就把过去和现在磨成了一团,分不清哪是陈味,哪是新香——但都一样,是日子该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