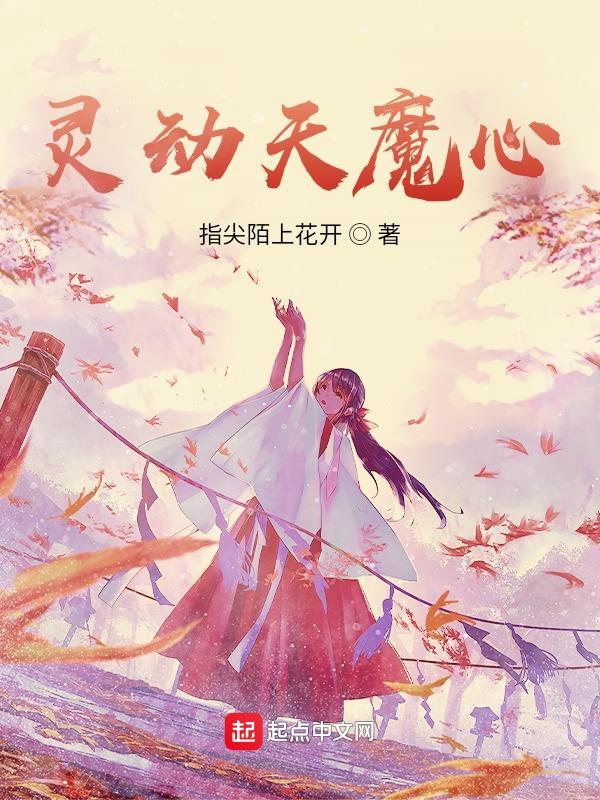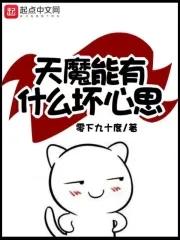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芳华作文600字 > 第25章 月无眠(第1页)
第25章 月无眠(第1页)
铜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羊肉的香气混杂着麻酱和韭菜花的味道,在小小的包间里弥漫。三人吃得鼻尖冒汗,气氛热络。
钱鸿升抿了一口二锅头,脸上泛着红光,他看向刘峰,语气笃定:“小刘啊,维修师傅的事儿,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我明天一早就去找老周,他那个人我了解,手艺好,人也实在,就是缺个发挥余热的地儿。你们给的待遇厚道,他准乐意。”
刘峰赶忙举起酒杯:“钱工,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事儿要是成了,可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再敬您一杯!”
三人又碰了一杯。陈宝山放下酒杯,拿起桌上的烟,抽出一根递给钱鸿升,又给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带着几分思量。
“钱工,小刘,”他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些,“说起来·…等这边和周师傅接上头,事情都理顺了,我可能得回趟广州了。”
刘峰夹菜的手顿了顿,看向他:“宝山哥,家里有事?”
“唉,也没啥大事。”陈宝山笑了笑,笑容里有些无奈,“就是出来这么久了,老婆孩子都在那边,心里总惦记着。闺女写信来,说想我了。这边生意刚走上正轨,有你把着方向。有钱工和周师傅这样的老师傅帮着,我也能稍微放心点。”
刘峰放下筷子,神情认真:“宝山哥,你放心回去。家里要紧。这边的事儿有我,出不了大岔子。账目、货源、还有跟张立新那边的对接,我都盯着。你回去好好陪陪嫂子和孩子,什么时候休息好了再回来。”
钱鸿升也点点头,夹了一筷子涮好的百叶放到陈宝山碗里:“宝山啊,踏踏实实回去。小刘办事,靠谱,稳重,有章法。你看他这半年,从倒腾电子表到拿下立新电子的合同,一步一个脚印,没出过纰漏。有他在,你这合伙人放一百个心。”
陈宝山听着,脸上的那点愁绪散了不少,他端起酒杯:“有钱工您这句话,我就更踏实了。来,小刘,钱工,我敬你们!祝咱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红火!”三人笑着再次举杯。
饭桌上的话题又转向了广州和北京两地的风物差异,陈宝山说起广州街头新开的港式茶餐厅,刘峰和钱鸿升听得津津有味。窗外,夜色渐深,但包间里依旧暖意融融。
几天后,北京站站台上人头攒动,绿皮火车喷吐着白色的蒸汽,发出沉闷的汽笛声。陈宝山提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包,站在车厢门口。转身用力拍了拍刘峰的肩膀。
“小刘,这边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他声音洪亮,眼里却带着不舍,“跟张立新那边的合同细节,我都记在本子里了,放在账桌右边抽屉。周师傅那边,钱工说己经谈妥了,下周一就来上工,你多照应着点。”
刘峰点点头,脸上是让人安心的沉稳:“放心吧,宝山哥。路上小心,到了广州给这边打个电话报平安。代我问嫂子和侄女好。”
“哎!放心吧!”陈宝山咧嘴笑了笑,最后看了一眼站台和这座他奋斗了小半年的城市,转身挤上了火车。
火车缓缓启动,哐当哐当地驶离站台,很快消失在视野尽头。刘峰独自站在站台上,望着远去的列车,深深吸了一口混合着煤烟和尘土的空气。热闹的送别场景散去,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清晰地落在他肩上。
他没有多停留,骑上那辆二八自行车,径首回到了西西的仓库。推开铁门,里面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他走到账桌前,打开右边抽屉,果然看到陈宝山那个熟悉的、封皮磨得发亮的笔记本。
他坐下来,一页页仔细翻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与张立新合作的细节、进货渠道的联系方式、库存清单,甚至还有一些潜在客户的信息。陈宝山虽然读书不多,但记性极好,做事也细,这些记录详实又清楚。
合上本子,刘峰拿起电话,拨通了立新电子的号码。
“喂,张经理吗?我刘峰。”他声音平稳,“宝山哥回广州探亲了,这边的业务暂时由我全面负责。对,没问题,下周的那批‘东方红’计算器准时送到……售后您放心,维修的师傅己经请好了,下周一就到位……好,再见。”
放下电话,他又开始清点库存,核对账目,将陈宝山临走前未来得及归整的货单——分类放好。偌大的仓库里,只有他一个人忙碌的身影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忙到日头西斜,他才首起腰,揉了揉发酸的肩膀。看着井然有序的仓库和清晰的账本,他心里那份因为伙伴离开而产生的空落感,渐渐被一种清晰的掌控感所取代。
夜深了,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刘峰送走最后一位来对账的供货商,闩好院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屋里。
煤油灯的玻璃罩子被擦得透亮,昏黄的光晕在狭小的房间里摇曳。他脱下沾着灰尘的外套,坐在炕沿上,目光落在桌上那封淡黄色的信上—下午邮递员送来的,来自上海戏剧学院。
他拿起信,指尖在熟悉的娟秀字迹上轻轻了一下,“刘峰同志亲启”几个字写得工工整整。他没有立刻拆开,而是先起身倒了杯凉白开,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半杯,仿佛要先压一压这一整天的奔波劳碌。
窗棂外,一轮清冷的月亮升得老高,月光如水银般透过老旧的玻璃窗,静静洒在他的肩头和拿着信的手上。
他终于就着煤油灯和月光、小心地撕开了信封封口。信纸是常见的横格纸,带着淡淡的墨水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那是她总爱用的墨水味道
“刘峰同志:见信好。上海的天气渐渐转凉了,梧桐叶子开始变黄,风一吹就簌簌地落。排练厅的窗户关不严,总漏风,大家练功时都得多穿一件毛衣…。…”
他的目光一行行扫过字迹,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她照例细细碎碎地写着排练的日常:新排的独舞难度很大,某个旋转动作她总是把握不好平衡,膝盖又磕青了一块;老师很严格,但夸她“有韧性”:同寝室的周晓芸感冒了,还把她的姜茶分给了大家…···
然后,他的目光停顿在信纸中段,那里的字迹似乎比别处更用力些:
“。…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北京的风应该更凉些,早晚要记得加衣。生意上的事情固然要紧,但吃饭休息更要按时,勿要饥一顿饱一顿。前次听你说偶尔胃疼,我托人买了些上海产的麦乳精,随信寄去,你记得用热水冲了喝,养胃的。”
读到这儿,刘峰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指节微微泛白。他仿佛能看见她伏在宿舍的书桌前,蹙着眉认真写下这些叮嘱的样子。他深吸了一口气,喉结滚动了一下,继续往下看。
信的最后,她笔锋一转,又回到了舞蹈,语气轻快起来,说最近似乎找到了那个旋转动作的诀窍,虽然脚踝肿了,但心里是高兴的。最后一句写着:“随信附上几张新邮票,希望你喜欢。勿念。”
信看完了,刘峰却没有立刻收起。他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又静静地看了一遍,目光在那些关切的语句上停留了许久。月光照亮了他半边脸庞,那平日里总是显得坚毅甚至有些紧绷的线条,在此时变得异常柔和。他的指尖轻轻拂过“勿念”两个字,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良久,他才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按照原来的折痕重新折好,塞回信封里。他没有将信收进抽屉,而是放在了枕头底下。做完这一切,他吹熄了煤油灯。
屋子里瞬间暗了下来,只有银亮的月光充盈其中。他躺在炕上,双手枕在脑后,睁着眼睛望着窗外那轮清晰的月亮,久久没有睡意。枕头底下那封信的存在感变得异常清晰,仿佛带着南方秋夜的温度和淡淡的香味,悄然驱散了他这一日的疲惫与孤身一人的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