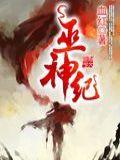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司马师曹髦 > 第42章 兄弟面前唱棠棣一曲挑出嫌隙来(第2页)
第42章 兄弟面前唱棠棣一曲挑出嫌隙来(第2页)
廊下光线昏暗,卷宗堆积如山,散发着陈年纸墨的霉味,混杂着木架受潮后析出的淡淡腐气,鼻腔深处泛起一丝酸涩。
蛛网悬于梁间,尘埃在斜射进来的微光中缓缓浮游,如同悬浮的星尘。
沈约慢条斯理地指挥着众人搬运,自己则在一排排木架间来回踱步,皮靴踏在朽木地板上,发出吱呀轻响,仿佛踩碎了时光的薄壳。
每一步落下,脚下木板轻微凹陷,传来沉闷的回响。
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转角,他袖中滑出一卷看似不起眼的账册,不偏不倚地掉落在积满灰尘的地面,激起一圈细小的烟尘。
尘粒扑上脚背,带来一阵痒意,旋即消散。
他眼角余光瞥了一眼,便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
这本账册乃是精心伪造的杰作。
封皮陈旧,纸张泛黄,记录着冀州卞彰所辖三处屯田粮仓历年的损耗,每一笔数目都详尽得无可挑剔。
翻动时,纸页发出干涩的沙沙声,边缘微卷,确似经年流转。
然而,在账册不起眼的夹层中,藏着一页用特制药水轻印的痕迹——色泽黯淡,边缘虚浮,既无年月标记,也未与其他文书骑缝相合,俨然是事后私自加盖。
更致命的是,账册末尾,仿着一位早己告老还乡的中书省老吏的笔迹,添了一行蝇头小字:“每岁多报耗粟三千斛,以充幕府私用。”墨色鲜亮,与泛黄纸页格格不入,宛如新伤覆于旧疤之上,指尖轻抚,尚能感受到微微凸起的墨痕质感。
这枚精心设置的鱼饵,静静地躺在黑暗中,等待着它命定的发现者。
果不其然,不出半日,这份“遗落”的账册便由一名惯会察言观色的宦官“无意”中拾得,并辗转送入了安东将军司马昭的府邸。
那宦官姓陈,名安,素来为安东将军府耳目。
他每日巡廊必经西库,今日忽见尘土中有异样卷宗,拾起一看,赫然写着“卞彰”二字——正是司马昭旧部。
心下一动,连夜托人转交府中幕僚荀勖。
书房内,烛火摇曳,映得墙上影子如鬼魅舞动。
窗外雨声初歇,檐滴敲打着石阶,一声,又一声,如同倒计时的鼓点。
司马昭手持那本薄薄的账册,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指尖抚过那行蝇头小字,忽觉墨色过于鲜亮,与泛黄纸页格格不入。
他心头一凛:“莫非是栽赃?”
但昨夜那声“阋于墙……阋于墙……”再次浮现耳畔,如芒刺在背。
若真是伪造,谁会有动机陷害我兄?若是真的,他又为何默许?
“传我密令,”他冷冷开口,“派两名心腹快马奔赴冀州,彻查三仓出入记录,务必查明近年实耗。若有遮掩,格杀勿论。”
荀勖垂手而立,神情恭谨,不急不缓地答道:“明公息怒。依属下之见,此事或为奸人伪作,意在离间大将军与明公昆仲之情,坐收渔翁之利。”
这话本该平息怒火,却如油浇烈焰。
司马昭闭目片刻,脑海中闪过兄长闭门谢客的身影,坊间传言其病重难理政事……
荀勖又看似不经意地补了一句:“不过,为求稳妥,明公可暗中派人查验冀州那几处粮仓近年的实际出入记录,以辨真伪。同时,近来坊间皆言大将军抱病不出,恐是对下情有所不察。”
诛心之言,字字穿骨。
若兄长知情,便是纵容贪腐,其清名何在?
若兄长不知,则意味着他对部下的掌控己然失控,大权旁落。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让司马昭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挥了挥手,让荀勖退下,独自在书房中枯坐良久。
接下来的三日,洛阳城看似平静。
但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