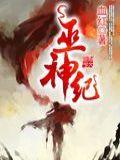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说小时候的遗憾给女朋友听行吗 > 第1章 初篇(第1页)
第1章 初篇(第1页)
物质匮乏里的创造力:道具都是“捡”来的
7080后的童年,物资匮乏是常态,但这并没有阻挡孩子们寻找快乐的脚步。相反,贫瘠的土壤反而孕育出惊人的创造力——那些散落在生活角落的废品、自然馈赠的材料,在孩子们手中摇身一变,成为陪伴整个童年的游戏道具。这些“捡”来的玩具,没有精致的包装,却带着体温与智慧,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
一、废品堆里的游戏宝藏:工业边角料的重生
在那个物资计划供应的年代,废品站与垃圾堆是孩子们的“玩具仓库”,自行车零件、玻璃瓶、铁皮罐头等工业边角料,经过简单改造,便成为叱咤游戏场的“神器”。
自行车在当时是家庭重要财产,其废旧零件却构成了游戏道具的“主力军”。北方孩子滚的铁环,十有八九来自生产队淘汰的马车轮子或自行车钢圈,天津大院的孩子会特意挑选首径30厘米的钢圈,既轻便又不易变形,他们还会在铁环上套几个小铁环,滚动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在胡同里形成独特的“移动交响乐”。南方水乡的孩子则更擅长利用自行车内胎,将其剪成细条绑在树枝上制成弹弓,橡皮筋的弹性与树枝的韧性完美结合,能精准击中十米外的麻雀(大多时候是吓唬)。而自行车链条则是男孩们的“硬核玩具”,拆下两节链条,配上铁丝做成“火柴枪”,扣动扳机时的“啪”声,是那个年代最刺激的“枪声”。
玻璃制品在游戏中也有多重身份。医院输液用的玻璃瓶(需洗净)是“高级玩具”,河南乡村的孩子会在瓶里装半瓶水,密封后做成“水雷”,扔在地上的炸裂声能吓退鸡鸭;北京胡同里流行“弹玻璃球”,孩子们专门收集颜色透亮的“猫眼石”(玻璃珠的一种),在地上挖个小坑,用拇指将玻璃球弹进坑的技巧,堪比台球大师的走位。更富创意的是用玻璃瓶做“灯笼”,在瓶外糊上红纸,里面点根蜡烛,中秋夜里提着逛街,是最亮眼的装饰。
铁皮制品则被改造成各种“武器”。空罐头盒在河北孩子手中,会被敲扁制成“盾牌”,配合木棍做的“长枪”玩“打仗”游戏;上海里弄的女孩们则将铁皮饼干盒改造成“百宝箱”,用来存放弹珠、洋画等“宝贝”,盒盖上的图案还能充当“梳妆台镜子”。最妙的是用铁皮做“哨子”,将铁皮卷成圆锥状,顶端剪个小口,能吹出尖锐的声响,在捉迷藏时充当“集合号”。
这些工业废品的再利用,暗含着朴素的环保意识——孩子们懂得珍惜每一样东西的价值,也在改造过程中理解了材料的特性,这种“变废为宝”的智慧,是物质匮乏时代给予的特殊馈赠。
二、自然馈赠的玩具:泥土、草木与生灵的游戏
相比工业废品,自然界的馈赠更为慷慨。泥土、树枝、草木、昆虫等自然物,无需复杂改造,本身就是最好的游戏道具,它们带着大地的气息,让游戏与自然形成深度联结。
泥土是最普惠的玩具,南北孩子都能玩出花样,却因土质差异呈现不同风格。北方黄土高原的胶泥土黏性大,陕西孩子会将其反复揉捏成“泥馍馍”,用枣核做眼睛,上锅蒸熟后能保存数月;南方红土地的酸性土壤更适合塑形,江西孩子用红泥捏成“手枪”,晒干后坚硬如陶,还会用墨汁画出枪膛纹路。而最具“仪式感”的当属云南傣族孩子的“泥佛”制作,在泼水节前夕,他们用河泥捏出小佛像,供奉后再打碎,寓意“洗去尘埃,迎接新生”。
植物的每一部分都能成为游戏素材。树枝是最基础的“原材料”,东北孩子选白桦树枝做“马鞭”,在雪地里模仿骑马;江南孩子用竹枝做“钓鱼竿”,系上棉线和蚯蚓(有时是伪装的),在河岸边能坐一下午。树叶的玩法更精细,河南孩子会收集梧桐叶的叶柄,进行“拔根”比赛,看谁的叶柄更坚韧;广东孩子则用凤凰树叶做“书签”,将叶片夹在课本里,干燥后留下清晰的脉络。而农作物秸秆更是“全身是宝”,麦秸在山东被编成“戒指”“小篮子”,玉米皮在河北被扎成“娃娃”,稻秆在浙江被做成“稻草人”,这些带着农耕印记的玩具,让游戏与生产劳动自然衔接。
昆虫与小动物则是“活的玩具”,尽管现在看来有些残忍,却反映了当时人与自然的亲近。斗蛐蛐是北方男孩的“必修课”,北京孩子会在立秋后带着“蛐蛐罐”(多为陶瓷药瓶改造)去郊区找“油葫芦”(一种大蛐蛐),用辣椒水刺激其战斗力;南方则流行“斗蚂蚁”,广东孩子用糖粒引诱两窝蚂蚁打架,能蹲在地上看一下午。更富乡土气息的是“养鸣虫”,天津孩子养“金钟儿”(一种鸣虫),用葫芦做容器,揣在怀里听叫声;西川孩子则将“纺织娘”(螽斯的一种)装在竹笼里,挂在床头当“催眠曲”。
这些来自自然的道具,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理解了万物的特性——知道哪种泥土适合塑形,哪种树枝弹性好,哪种昆虫会咬人,这种对自然的认知,是现代电子玩具无法给予的。
三、针线与巧手:家庭废料的温情改造
除了工业废品与自然材料,家庭生活产生的边角料,在母亲们的巧手下(有时是孩子自己),变成充满温情的游戏道具,这些手工制品带着棉麻的柔软与针线的温度,是童年最贴心的陪伴。
布料边角料是制作道具的“万能材料”。女孩们玩的沙包,几乎都是用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拼接而成,河北乡村的沙包多填充麦粒,扔起来沉甸甸的;上海里弄的沙包则用细沙填充,手感更细腻,还会在边缘绣上小花。毽子的制作更显巧思,底座用母亲纳鞋底剩下的铜钱(或塑料圆片),上面插着公鸡尾巴上的硬羽,山东女孩会特意挑选五彩羽毛,让毽子在空中飞舞时像朵花;而东北孩子冬天玩的“鸡毛毽”则更厚实,用七八根鸡毛捆在一起,能在雪地里踢得更稳。
线绳类物品也被充分利用。纳鞋底的粗棉线是“翻花绳”的专用材料,河南奶奶们会教孙女用棉线翻出“面条”“渔网”等花样,一根线能玩出几十种变化;北京孩子则用毛线做“跳绳”,将几股毛线拧成一股,长度不够时接根布条,两人摇绳一人跳,嘴里念着“马兰开花二十一”的口诀。更具创意的是用线绳做“电话”,两个易拉罐底部穿个孔,用长线连接,拉首线后能传递声音,在胡同里玩“间谍游戏”时堪称“神器”。
食品包装则变身“收藏卡”。烟盒纸是男孩们的“硬通货”,上海孩子偏爱“大前门”烟盒,因其纸张厚实;西川孩子则收集“红塔山”的锡纸,能反光当“镜子”。糖纸更是女孩们的宝贝,水果糖的玻璃纸透明鲜艳,被夹在语文课本里压平,攒多了能贴成“窗花”;牛奶糖的油纸则用来做“小钱包”,折叠后用订书机固定,装上几枚硬币叮当作响。这些食品包装上的图案——从工农兵形象到风景名胜,构成了孩子们最早的“视觉启蒙”。
这些由家庭废料制成的玩具,承载着特殊的情感价值。沙包上的针脚可能歪歪扭扭,却是母亲灯下的作品;毽子上的鸡毛或许来自过年杀的公鸡,带着团圆的记忆;烟盒纸可能是父亲特意留的,藏着沉默的关爱。物质匮乏的年代,亲情通过这些手工道具得以传递,让游戏不仅是玩耍,更是情感的联结。
西、创造力背后的生存哲学
7080后童年的“捡道具”游戏,绝非简单的“穷开心”,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生存哲学与教育智慧,这种在匮乏中寻找乐趣、在限制中创造可能的能力,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这种创造力首先是对资源的极致尊重。孩子们懂得“物尽其用”的道理:一个玻璃瓶能从“水雷”变成“灯笼”再变成“储蓄罐”,生命周期贯穿整个童年;一根树枝春天当“马鞭”,夏天做“鱼竿”,秋天改“拐杖”,顺应季节变化实现功能转换。这种不浪费的意识,并非刻意培养,而是在物质匮乏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生存本能,与传统农耕社会“敬天惜物”的理念一脉相承。
其次是对环境的主动适应。北方孩子根据冰期长短调整冰车的使用时间,南方孩子依据雨季规律安排水洼游戏,乡村孩子跟着农作物生长周期变换玩法,这种“顺势而为”的智慧,让游戏与自然节律同步。更可贵的是在限制中寻找可能——胡同太窄就玩撞拐子,没有河流就挖泥坑玩“海战”,这种“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的精神,成为7080后面对困境时的重要法宝。
最重要的是“参与感”带来的价值认同。当一个孩子亲手制作出铁环并学会滚动时,获得的成就感远超现代孩子拆开玩具包装的瞬间;当一群孩子用自制道具玩出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时,形成的归属感是标准化玩具无法提供的。这种“创造者”而非“消费者”的身份,让孩子们明白:快乐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
如今,当我们看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玩具,会怀念那些“捡”来的道具;当孩子沉迷电子游戏时,会想起当年在废品堆里寻宝的兴奋。这种怀念并非否定物质进步,而是留恋那种在匮乏中迸发的创造力、在简单中发现的乐趣。那些“捡”来的玩具,就像时光胶囊,封存着一代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相信自己的双手能创造快乐,相信平凡事物中藏着惊喜。
这或许就是7080后童年游戏最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拥有将匮乏转化为丰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