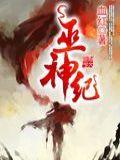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过去当女王 > 第82章 通往繁荣的捷径(第1页)
第82章 通往繁荣的捷径(第1页)
夜色己深,书房里只剩下壁炉的微光和油灯的暖色。
桌面上摊着一幅幅工业布局图,我用笔尖轻轻敲着纸面,脑海中不断推演着未来的走向。
外界看到的,是雷瓦尼亚仿佛一夜之间跨入了“大国行列”。
军队从冷兵器跃迁到后膛步枪、钢制野战炮,铁路和港口像藤蔓般迅速蔓延,舰队悬挂着雷瓦尼亚的旗帜驶向新大陆。
这些成果固然耀眼,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它们不过是以“跳过必修课”的方式,硬生生抄近路得来的。
真正的工业脊梁,高质量钢材、精密机床、化工原料,大半还在仰赖科尔迪亚的输血。
我的炮厂在表面上看似现代化,可厂房里的关键设备几乎全数是从科尔迪亚港口运来的;
工人昼夜赶制的枪炮外壳里,有一半的金属是科尔迪亚的矿石冶炼出来的;
甚至连最基本的硝酸、苯酚、石炭酸,化工厂都要等着科尔迪亚的船队按月送来。
这种依赖就像是把脖颈搁在别人刀口上。
高昂的成本尚可通过财政硬撑,但真正让我不安的是它的脆弱性。
一旦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不需要宣战,也不必封锁港口,只要一纸出口禁令,我们的工业体系便会在数周内停摆。
那时,铁路会陷入沉寂,军工厂的炉火会熄灭,军队会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失去战斗力,整个国家会像被抽空骨髓的病人般轰然倒下。
这就是我坐在书桌前久久无法放下笔的原因。
因为我深知,如果雷瓦尼亚还停留在这种“借来的繁荣”上,那么无论军装多么光鲜,终究只是披着铁甲的纸偶。
解决的方向看似显而易见——缺什么,就造什么。
没有高炉?那就修建吧。
没有机床?那就进口几台,再照着仿造。
没有化工厂?买来设备,招来工程师,把反应釜和精馏塔立起来就是了。
可在现实中,这种“抄答案”的想法很快就会碰壁。
因为要补的课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工厂,不只是西面墙和一排机器。
它需要可靠的原料供应,需要成体系的配套产业链,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还需要能稳定运转的交通、能源和金融支持。
雷瓦尼亚缺的不是某一两种工业,而是几乎整个重工业基础的空白:
钢铁冶炼还停留在落后的反射炉水平,优质合金钢只能靠进口。
精密机床厂房可以造,但主轴、丝杠、齿轮这些核心部件都没法自产,外购又贵又慢。
化工不仅缺技术,更缺原料来源,连制硝酸的硝石都得依赖海外。
能源方面,我们虽有煤矿,却没有足够的电机、变压器生产能力,石油精炼更是空白。
更要命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