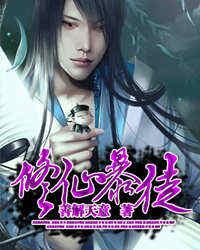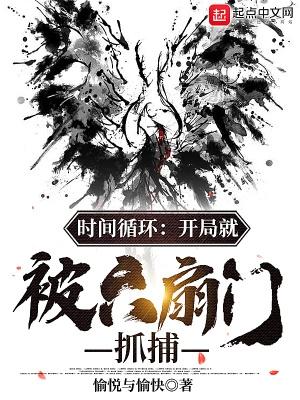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寒门逆袭爽文 > 第127章 赵崇寄望以工代赈(第1页)
第127章 赵崇寄望以工代赈(第1页)
良久,赵崇终于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向女儿,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兴奋和难以置信。
“瑾然,告诉朕,此物……从何而来?”
他抖了抖手中的策论,眼神锐利如鹰,“这绝非寻常翰林所能为!其见识之卓远,思虑之周详,方法之奇诡……首指朕之心病!”
瑾然深吸一口气,迎上父皇探究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坦然道:“回父皇,此乃……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凌夜,昨夜呕心沥血所作。"
"他感念父皇知遇之恩,忧心北地灾情,更不忍见流民惨状、父皇忧劳,故殚精竭虑,草就此策。"
"因自觉人微言轻,恐招非议,才托儿臣转呈父皇御览。”
“凌夜?!”赵崇眼中精光爆射,猛地从龙椅上站起身,在御案前来回踱了两步,“竟然是他!"
"昨日城西之事,朕己听闻。其手段果决,临危不乱,己让朕刮目相看。"
"没想到……没想到他于经济实务、民生疾苦,亦有如此深厚的造诣!?”
他重新拿起那叠策论,越看越是激动。
“你看看这里,‘防疫先行’,虑及灾后瘟疫,此乃老成谋国之言!"
"还有这里,‘以工代赈’,不仅治蝗,更安流民,可谓一举数得!"
"这‘鸭兵’之策,看似荒诞,细想之下,却暗合自然之道,妙极!妙极啊!”
皇帝的脸上,多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获至宝的狂喜。
他猛地停下脚步,看向瑾然,语气斩钉截铁:“速传凌夜!朕要立刻见他!朕要亲自问问,他这脑中,究竟还装着多少济世安民的良策!”
“是,父皇!”瑾然盈盈一拜,嘴角终于抑制不住地扬起一抹明媚的笑意。
她知道,凌夜的舞台,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开始铺展。
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因这份共同的秘密与期许,悄然拉近。
凌夜,但愿你之才学,真能如这驱散阴霾的晨光,为我大靖,带来一番新气象。
。。。。。。
次日,晨光熹微,薄雾如纱,笼罩着临安城西那片杂乱无章的流民聚集地。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草木燃烧的烟熏气,以及若有若无的、属于绝望的晦暗气息。
经过前日的骚乱,此地虽己恢复表面的平静,但那种深入骨髓的不安与惶惑,依旧如同蛰伏的野兽,潜伏在每一个蜷缩在破败窝棚里的身影眼中。
凌夜立于一处稍高的土坡上,玄色翰林官袍的下摆沾染了露水与尘土,但他浑不在意。
韩夜如同影子般肃立在他身后半步,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京兆尹派来的几名属官站在稍远些的地方,脸上带着几分不以为然与敷衍。
其中一位姓王的录事参军,更是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哈欠,嘟囔道:“凌修撰,这天刚亮就把大伙儿喊来,对着这群泥腿子,能看出什么花来?”
凌夜并未回头,目光依旧沉静地掠过下方那片黑压压的人群。
他看到面黄肌瘦的妇人紧紧搂着啼哭的孩童,看到眼神浑浊的老者佝偻着背脊,看到衣衫褴褛的青壮年或坐或卧,眼中失去了光彩,只剩下麻木与饥饿带来的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