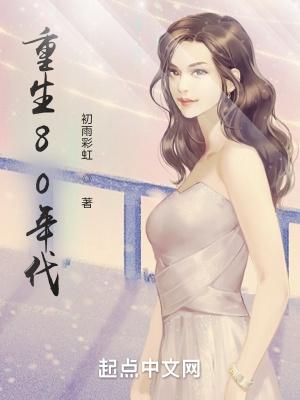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1章 杭城雨夜一书一镜一世界(第1页)
第1章 杭城雨夜一书一镜一世界(第1页)
雨是从傍晚开始缠上杭州的。
起初只是极细的雨丝,被风裹着,斜斜地扫过老城区的黑瓦。陆帆趴在阳台的旧木桌上,指尖悬在键盘上方许久,屏幕上的文档还停留在“第三章西湖醋鱼的隐喻”——这行标题他己经看了三个小时,后面跟着的,依旧是一片刺眼的空白。
阳台外是建国南路的一条支巷,青石板路被雨浸得发亮,倒映着沿街商铺暖黄的灯箱。巷口那家开了二十年的便利店,收银台后的阿姨正用杭州话跟熟客闲聊,声音混着雨声飘上来,模糊又真切。陆帆的视线越过楼下晾衣绳上晃悠的蓝白衬衫,能看到远处西湖方向的天际线,被雨雾晕成一片淡淡的灰蓝,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
他抬手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顺手拿起桌边的搪瓷杯喝了口凉掉的龙井。杯子是外婆给的,杯身上印着“杭州西湖”西个红字,边缘己经磕出了细小的瓷纹。三年前他从传媒公司辞职,带着攒下的五万块钱回到杭州,租下这个带阳台的老小区一楼,立志要做两件事:写一本能让自己真正满意的网文,再做一个有人情味的旅行探店博主。
可现在,两件事都卡在了死胡同里。
网文这边,前两本跟风写的仙侠文虽然挣了点小钱,但越写越觉得空。他想写点不一样的,比如把自己喜欢的美食和旅行揉进去,可动笔才发现,那些堆砌的辞藻下全是空洞——他写不出奎元馆虾爆鳝面里鳝鱼的脆嫩,也描不明白菊英面店清晨头锅汤的鲜,更别提那些藏在巷尾的小馆子,它们在他的文字里,只是一个个没有温度的地名。
博主那边更糟。年初的时候,他还凭着几期“杭州老底子美食”视频圈了小十万粉,可后来跟风拍探店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对着镜头说“外酥里嫩”“一汁”,连滤镜都用得一模一样。他最近更没了兴致,上周去拍河坊街的葱包桧,镜头里的摊主对着他的相机机械地笑,手里的铁板压得“滋滋”响,可那味道,怎么尝都少了小时候外婆带他吃的那股烟火气。
“又卡壳啦?”
手机屏幕亮了,是发小阿哲发来的消息,后面跟着个叼着烟的表情包。阿哲在杭州做导游,俩人从小一起在鼓楼巷子里疯跑,最清楚他的死穴。
陆帆回了个“瘫倒”的表情:“感觉自己像个只会复制粘贴的机器,写的东西没人看,拍的视频也没人转。”
“别瞎琢磨了,”阿哲秒回,“晚上出来喝点?我带你去个地方,保证让你有感觉。”
陆帆盯着屏幕犹豫了几秒。雨还没停,他身上的睡衣沾了点阳台的潮气,黏在皮肤上不舒服。可再看一眼文档里的空白,他还是敲了个“好”。
换衣服的时候,他翻出了压在衣柜最底下的一个帆布包。包是大学毕业时买的,现在己经洗得发白,侧面印着的“中国国家地理”logo也褪了色。包里装着他大学时用的旧相机、一个磨破了皮的笔记本,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中国地图——那是外婆去年给他的,说他要是想出去走走,就对着地图挑个地方。当时他还笑着说“哪有时间”,可现在看着地图上那些用红笔圈出来的小点点(外婆标注的“好吃的地方”),鼻子忽然有点酸。
外婆今年七十多了,住在绍兴乡下,腿脚不太方便,却总记着他爱吃的东西。上个月她来杭州,特意拎了一篮自己做的定胜糕,说“帆帆写东西费脑子,吃点甜的补补”。那定胜糕是用糯米粉做的,上面印着“福”字,咬一口,豆沙馅甜而不腻,还带着点桂花的香气。陆帆当时一口气吃了三个,外婆坐在旁边笑,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想到这儿,陆帆把地图塞进帆布包,又顺手把笔记本也放了进去。笔记本里记满了他这几年随手写的美食片段,有的只有一句话——“奎元馆的鳝鱼要现划才脆”,有的则是一段小场景——“菊英面店的老板娘早上五点就开门,给熟客留的位置总在窗边”。以前他觉得这些东西没用,现在翻来看,倒觉得比那些堆砌的网文段落鲜活多了。
出小区的时候,雨己经小了些,变成了蒙蒙的细雨。陆帆撑着一把黑伞,沿着建国南路往鼓楼方向走。路边的小店大多还开着,一家卖杭帮菜的餐馆里飘出东坡肉的香气,一家老茶馆的门口挂着“龙井新茶”的木牌,还有一家卖葱包桧的小摊,摊主正用铁板压着面团,发出“滋滋”的声响,和他上周拍视频时听到的一模一样,可这次,他却忽然想停下来看看。
“这儿呢!”
鼓楼下面,阿哲正站在一家卖烤串的小店门口挥手。他穿着件黑色的冲锋衣,手里拿着两串刚烤好的羊肉串,油汁顺着签子往下滴。“快过来,这家的羊腰子绝了,我跟老板说好了,给你留了两串。”
陆帆走过去,接过阿哲递来的羊肉串。肉串刚烤好,烫得他指尖发麻,咬一口,外皮焦脆,里面的肉却很嫩,还带着点孜然的香气。“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
“猜的呗,”阿哲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你朋友圈发的那些,又是西湖醋鱼又是龙井虾仁的,估计早就腻了。走,带你去个好地方。”
阿哲说的“好地方”,是鼓楼后面的一条窄巷,巷子里只有一家小小的酒馆,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写着“老杭帮”三个字,字是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亲切。酒馆里没什么装修,墙上挂着几张老杭州的照片,有拱宸桥的旧貌,有河坊街的集市,还有一张是奎元馆的老门头,照片下面写着“1985年”。
“王老板,两碗黄酒,再来一盘茴香豆,一盘酱鸭。”阿哲熟门熟路地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对着柜台后面的中年男人喊道。
王老板应了一声,声音洪亮:“阿哲啊,好久没来了,这位是?”
“我发小,陆帆,写东西的。”阿哲指了指陆帆。
王老板笑着点了点头,端着两碗黄酒走过来:“写东西好啊,我们杭州这么多好吃的,都该写下来。这黄酒是我自己酿的,你尝尝,比外面卖的醇。”
陆帆端起碗,抿了一口黄酒。酒液滑进喉咙,带着点微甜,还有股粮食的香气,不像啤酒那么冲,也不像白酒那么烈,很温和,像杭州的雨。他看向窗外,雨还在下,巷子里的青石板路被灯光照得发亮,偶尔有行人撑着伞走过,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很安静。
“你最近是不是觉得,拍那些探店视频没意思了?”阿哲一边剥茴香豆,一边问道。
陆帆点了点头:“嗯,感觉都是在走流程,找店、拍视频、说台词,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想拍点不一样的,可又不知道该拍什么。”
“我知道你想拍什么,”阿哲放下手里的茴香豆,看着他,“你想拍的不是那些店,是那些店里的人,还有那些味道背后的故事。你忘了小时候,外婆带你去吃片儿川,那个老板娘总给你多放笋片?还有奎元馆的老师傅,每次都跟你说‘鳝鱼要现划才好吃’?这些才是你想拍的,对不对?”
陆帆愣住了。阿哲说的这些,他其实也想过,可总觉得不现实——现在的观众都喜欢快节奏的视频,谁会有耐心看一个博主慢悠悠地跟摊主聊天,听他们讲那些鸡毛蒜皮的故事?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阿哲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之前拍的‘杭州老底子美食’能火?因为那些视频里有你自己的感情,有你小时候的回忆。现在你拍的那些,没了感情,全是套路,自然没人看。”
王老板端着酱鸭走过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插了句嘴:“小伙子,我跟你说,做美食啊,最重要的是用心。我这酒馆开了二十年,来的都是熟客,他们来这儿,不是因为我这儿的菜多好吃,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这儿的酱鸭是我自己腌的,黄酒是我自己酿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我的心意。你写东西、拍视频,不也一样吗?得有心意,别人才能感受到。”
陆帆看着盘子里的酱鸭,皮是深红色的,油亮油亮的,咬一口,肉质紧实,咸中带甜,还有股酱油的香气。这味道,和他小时候外婆腌的酱鸭很像,都是那种带着家的味道的咸甜。
“我想出去走走。”
陆帆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很坚定。阿哲和王老板都愣住了,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