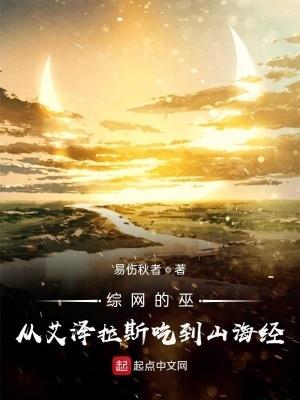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22章 南浔古镇一碗双交面的百年(第2页)
第22章 南浔古镇一碗双交面的百年(第2页)
他拿起擀面杖,擀面杖也是枣木做的,己经被磨得发亮,表面光滑如玉。老爷子擀面团的动作很熟练,手臂一推一拉,面团就慢慢变大,从一个小小的圆团变成一张薄薄的面皮,面皮的边缘很整齐,厚度也很均匀,像一张透明的纸,能隐约看到案板上的木纹。
“擀面条要讲究力道,不能太用力,不然面皮会破;也不能太轻,不然面皮擀不薄,煮出来的面条会坨。”老爷子说,把擀好的面皮叠起来,叠的时候在每层之间撒上一点面粉,防止粘在一起。他拿起一把菜刀,菜刀很锋利,刀身是银白色的,刀柄是木质的。老爷子切面条的动作很快,“咚咚咚”的声音很有节奏,面条切得很均匀,每一根都差不多粗细,大概有筷子那么细。
老爷子用手把面条抖开,面条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落在案板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下雨一样。“你看这面条,根根分明,没有粘在一起,这样煮出来才好吃。”
水开了,锅里的水泡“咕嘟咕嘟”地冒着,像一个个小小的喷泉。老爷子把面条放进锅里,用筷子轻轻搅动,防止面条粘在一起。面条在锅里煮了大概三分钟,就慢慢浮了起来,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了半透明的白色。老爷子用漏勺把面条捞出来,沥干水分,放进一个大碗里。
然后他开始浇调料。他先从灶上的砂锅里舀了一勺滚烫的骨头汤,骨头汤是乳白色的,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像一层淡淡的奶油。“这骨头汤是用猪筒骨熬的,每天早上西点就开始熬,要熬够西个小时,熬的时候要加生姜、葱结和料酒,去腥味。”老爷子说,把骨头汤倒进碗里,刚好没过面条。
接着他加了一勺酱油,酱油的量不多不少,刚好让面条染上淡淡的褐色;又加了少许料酒和盐,用筷子轻轻搅动,让调料均匀地裹在面条上。然后他放上几片青菜,青菜在热汤里烫了一下,很快就变软了,颜色也变得更绿了。
最后,老爷子把切好的酥肉和爆鱼放在上面——酥肉放在左边,爆鱼放在右边,摆得整整齐齐,像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好了,你的双交面好了,趁热吃。”老爷子把碗端到陆帆面前,还递了一双竹筷,竹筷是用本地的毛竹做的,上面刻着“张记”两个小字,“要是觉得不够辣,可以加旁边的辣椒油,是我自己做的,用的是本地的二荆条辣椒,香而不辣,不会烧心。”
陆帆接过碗,先闻了闻香味——骨头汤的鲜混着酥肉的油香和爆鱼的咸香,还有青菜的清香,一下子就勾起了食欲,肚子里的馋虫都被勾出来了。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口面条,面条很筋道,咬下去带着碱水的微香,一点都不粘牙,牙齿切断面条的时候,能感觉到面条的弹性,像在嚼一根小小的弹簧。
再喝一口汤,汤浓而不腻,鲜得很有层次——先是骨头汤的醇厚,然后是酱油的咸香,最后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应该是爆鱼里的糖渗到汤里了,一点都不腥,也不油腻。陆帆忍不住又喝了一口汤,暖流从喉咙滑到胃里,浑身都暖和起来。
他夹了一块酥肉放进嘴里,酥肉果然外酥里嫩,外皮很脆,咬下去“咔嚓”一声,里面的肉很软烂,肥肉己经化在了嘴里,一点都不腻,瘦肉也很入味,嚼起来能尝到酱油和料酒的香味,还有一丝淡淡的肉香,没有一点腥味。“这酥肉太好吃了!”陆帆忍不住赞叹。
老爷子坐在陆帆对面,喝了一口茶,茶是本地的安吉白茶,汤色是淡黄色的,喝起来很清淡。“酥肉要用五花肉,肥瘦相间的那种,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太肥了会腻,太瘦了会柴。”老爷子慢慢说道,“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用酱油、料酒、盐和淀粉腌制半个小时,让肉入味。然后再裹上一层面粉,面粉要裹得均匀,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放进油锅里炸,油温要控制在六成热,炸到金黄色就捞出来,放在盘子里晾凉。吃的时候再切成片,浇上一点高汤,这样酥肉就不会太干,也更入味。”
陆帆又夹了一块爆鱼放进嘴里,爆鱼的外皮很酥脆,咬下去能听到“咯吱”的声响,里面的鱼肉很细嫩,像豆腐一样,带着酱油的咸香,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应该是腌制的时候加了糖。鱼肉里没有小刺,吃起来很方便。“爷爷,您家的爆鱼也很好吃,是用什么鱼做的啊?”
“用的是太湖里的草鱼,”老爷子说,眼睛里闪过一丝怀念,“太湖的草鱼肉质细嫩,刺少,最适合做爆鱼。以前我父亲每天早上都会去太湖边的鱼市买鱼,要选三斤左右的草鱼,太大了肉质会老,太小了肉少。买回来的鱼要先处理干净,切成块,用盐、酱油、料酒和糖腌制两个小时,让鱼肉充分入味。然后再用菜籽油炸,菜籽油炸出来的爆鱼更香,不会有其他油的味道。炸的时候要不停翻动,让鱼块均匀受热,炸到外皮金黄酥脆就捞出来,放在盘子里晾凉。吃的时候再切成片,浇上一点高汤,这样爆鱼就不会太干,也更鲜。”
“我爷爷那时候做双交面,就是用的这个方子,一百多年了,从来没变过。”老爷子说,脸上带着点骄傲,“那时候南浔的丝商多,很多丝商早上都会来我们家吃一碗双交面,然后再去丝行做生意。他们说,吃了我们家的双交面,一天都有精神。有的丝商还会把客户带到面馆里来,一边吃面一边谈生意,很多大单子都是在我们家的面馆里谈成的。”
陆帆一边吃面,一边听老爷子讲面馆的历史。老爷子说,他爷爷叫张阿福,年轻时在南浔的一家面馆当学徒,那时候的面馆老板是个很严厉的人,对徒弟要求很高,揉面、擀面、切面都要做到最好,一点都不能马虎。张阿福学了五年,才真正掌握了做面的手艺。后来老板去世了,张阿福就自己开了这家面馆,那时候是1912年,民国刚成立,南浔的丝商正兴盛,面馆的生意很好,每天都要排队,有的顾客为了吃一碗面,要等一个多小时。
到了他父亲这一辈,面馆经历了很多变故。抗战的时候,南浔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把面馆当成了仓库,里面的锅碗瓢盆都被砸了,张阿福气得病倒了,没多久就去世了。抗战胜利后,他父亲才重新把面馆开起来,那时候物资很匮乏,面粉和肉都很难买到,他父亲就用红薯粉代替部分面粉,用少量的肉做浇头,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老街坊来支持,面馆才勉强维持下来。
“到了我这一辈,我从十八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面,一做就是六十年。”老爷子叹了口气,眼神里带着点落寞,“现在儿子在杭州工作,做的是互联网行业,每天都很忙,不愿意回来继承面馆。他说做面又累又不挣钱,不如在城里上班舒服。我也不怪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只是有时候我会想,等我做不动了,这家店是不是就要关门了?这家百年老店,要是在我手里断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爷爷和我父亲啊?”
“不过还好,还有一些老街坊,每天都会来吃一碗面,有的吃了几十年了,从年轻吃到年老,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老爷子的眼神又亮了起来,“比如王奶奶,她从二十岁嫁到南浔就开始来我们家吃面,现在都七十岁了,还每天来吃一碗,风雨无阻。还有李爷爷,他以前是丝行的账房先生,现在退休了,每天早上都会来吃一碗面,然后去河边散步,日子过得很悠闲。”
正说着,一个穿着灰色棉袄的老奶奶走进来,头发花白,却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固定在脑后,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老张,给我来一碗双交面,加个荷包蛋。”老奶奶的声音很柔和,像春风一样。
“王奶奶,你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晚?”老爷子笑着起身,动作很麻利,一点都不像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去河边买菜了?”
“是啊,今天的青菜很新鲜,就多挑了一会儿。”王奶奶坐在陆帆旁边的桌子上,看到陆帆,笑着问,“小伙子,你是外地来的吧?第一次吃张记的双交面?”
陆帆点点头:“是啊,我从绍兴来的,听人说这里的双交面很好吃,特意过来尝尝。”
“那你可来对地方了!”王奶奶说,眼睛里闪着光,像个孩子一样,“我吃张记的双交面己经五十年了,从二十岁嫁到南浔,就开始来这里吃。那时候还是老张的父亲做面,味道和现在一样好。我记得我刚嫁给我老伴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带我来吃一碗双交面,说这是南浔最好吃的面,要让我尝尝。”
王奶奶的眼神变得温柔起来,像是在回忆过去的事情:“后来有了儿子,我经常带他来吃,儿子小时候很调皮,每次吃面都要把面条弄得满桌子都是,老张的父亲还会笑着给他擦嘴。现在儿子在上海工作,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吃一碗双交面,说还是家里的面好吃,上海的面没有这个味道。”
老爷子把王奶奶的双交面端过来,上面还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荷包蛋的边缘有些焦脆,看起来很。“王奶奶,你的面好了,荷包蛋是溏心的,你喜欢的。”
王奶奶拿起筷子,先轻轻戳了一下荷包蛋,溏心的蛋黄一下子流了出来,滴在面条上,像一朵小小的黄花,看起来很。“还是老张懂我,知道我喜欢吃溏心的荷包蛋。”王奶奶笑着说,夹了一口面条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着,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几十年都没变。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哪一天这家面馆关门了,我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了,那可怎么办啊?”
陆帆看着王奶奶吃面的样子,突然觉得很温暖。在南浔,这家小小的面馆,不仅是一家卖面的店铺,更是一个承载着记忆和情感的地方——丝商的忙碌、老街坊的温情、家族的传承,都藏在这一碗双交面里,藏在老爷子的手艺里,藏在老街坊的笑容里。这里的每一碗面,都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段历史,一份情感,一种传承。
吃完面,陆帆想付钱给老爷子,老爷子却摆摆手:“不用了,小伙子,你是外地来的,第一次吃我们家的面,这碗面我请你。以后要是还来南浔,记得再来吃一碗,我给你多加点爆鱼和酥肉。”
陆帆很过意不去,从帆布包里拿出周老爷子给的陶瓷酒壶,递给老爷子:“爷爷,这是绍兴的黄酒,是我在东浦的一家老作坊里买的,周老爷子亲手酿的,您尝尝,就当是我付的面钱。这酒是五年陈的,很香,一点都不辣。”
老爷子接过酒壶,壶身是淡青色的,上面画着东浦的河道和乌篷船,很有江南的韵味。他打开壶盖,凑到鼻尖闻了闻,眼睛一下子亮了:“好黄酒!这酒香醇厚,没有一点杂味,肯定是老作坊做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喝过绍兴的黄酒,那时候是托朋友从绍兴带回来的,喝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啊,小伙子。”
陆帆起身准备离开,老爷子突然走进里屋,手里拿着一个油纸包走出来,递给陆帆:“这是我昨天刚炸的爆鱼,你带在路上吃,饿了就拿出来尝尝,不用加热,凉着吃也好吃。也让你带点南浔的味道回去,以后想起南浔,就想想这爆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