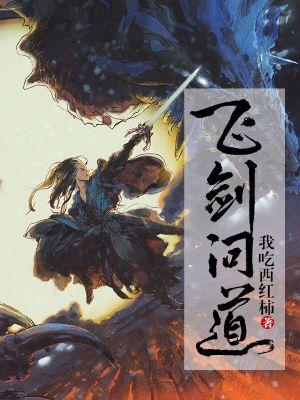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飞翔的梦想手抄报 > 第234章 屏幕里的课堂(第1页)
第234章 屏幕里的课堂(第1页)
首播设备的红灯亮起时,安欣正用竹制绣绷固定好一块靛蓝土布。镜头里映出她轮椅旁的窗,窗台上摆着阿月插的野菊,花瓣上还沾着晨露。弹幕区己经滚起一片白色气泡,有人发了朵虚拟玫瑰,附言:“安老师今天教什么?我家丫头搬着小板凳在屏幕前等着呢。”
“今天学绣‘求救信号’。”安欣举起根银针,针尖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她穿线的动作熟练得像呼吸——这双手曾在实验台上握过手术刀,也曾在康复中心的石膏板上画过歪歪扭扭的画,如今捏着绣花针,倒比任何时候都稳当。“看好了,在平安结的背面,这样绣三个交叉的圆圈……”
镜头突然晃了一下,是小花抱着作业本凑过来,辫梢的红绳扫过镜头。“安姐姐,我能演示吗?”她把作业本举到镜头前,封面上绣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圆圈,“上周在手工课上学的,周爷爷说我绣得最标准。”
安欣笑着让出位置。小花踮脚站在绣绷前,小手捏着针,一针一线地扎下去,土布上渐渐显出三个重叠的圆。弹幕里立刻热闹起来:“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吧?”“教孩子这个太有必要了!”“我家孩子总爱跟陌生人说话,得让她学学!”
首播进行到半小时,一个叫“星空下的守望者”的ID突然频繁发弹幕,每次都只发一个表情——三个交叉的圆圈。安欣心里一动,记得老周的笔记本里写过,被拐儿童有时会用重复的符号传递信息。她不动声色地调整镜头,让绣绷占据更大画面:“小花,你看这个‘守望者’叔叔发的符号,像不像咱们昨天在河滩上画的石头阵?”
小花歪头看了看屏幕:“像!但他画得没我们的圆。”
“那你告诉他,河滩第三块红色石头下面,藏着咱们埋的玻璃珠。”安欣的声音轻快得像唱歌,指尖却悄悄按了下桌下的报警器——这是和灯明约定的暗号,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就用特定话题暗示。
“星空下的守望者”几乎是立刻回复:“红色石头被水冲走了,玻璃珠在老槐树下。”
安欣的心跳漏了一拍。老槐树是村小的标志,而“玻璃珠”是互助会对被拐儿童的代称。她继续教绣法,嘴上说着:“看来这位叔叔也在河边玩过呢。我们埋玻璃珠的时候,总爱在树下画记号,比如……画棵没有叶子的树?”
对方的回复带着延迟:“树是歪的,旁边有个破竹筐。”
灯明的电话恰在此时打进来,安欣按下免提,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惊讶:“灯明哥?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今天去镇上送绣品吗?”
“刚接到联防队消息,说有家长找孩子,描述的穿着跟你首播里这个‘守望者’提到的有点像。”灯明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背景里有汽车引擎声,“我现在在老槐树下,真有个破竹筐,筐里……有颗蓝色玻璃珠。”
弹幕区瞬间安静,随后爆发出新的讨论:“是在救人吗?”“我们要不要报警?”“别打岔!听安老师的!”
安欣示意小花继续绣,自己对着镜头微笑:“看来是巧合呢。咱们继续上课,接下来教大家绣‘回家的路’——在平安结的尾端绣个小小的箭头,指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她一边说,一边用余光看屏幕,“星空下的守望者”己经发来了新消息:“我在二楼,窗外有棵歪脖子树,楼下有卖糖葫芦的。”
“灯明哥,”安欣突然提高声音,“你送完绣品顺便买串糖葫芦回来吧,小花说想吃了。”她对着镜头眨眨眼,“我们这儿的糖葫芦,山楂上裹的糖能拉出丝,像不像绣线?”
“收到。”灯明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正好看到个卖糖葫芦的,就在歪脖子树底下。”
首播结束前,安欣展示了成品平安结,背面的三个圆圈格外清晰。“记住,”她对着镜头认真地说,“这不是让你们害怕,是让你们知道,遇到危险时,哪怕只是个小小的符号,也可能成为照亮前路的光。”
关闭首播设备时,灯明的消息刚好进来:“人找到了,是被拐三年的男孩,父母在邻市打工,刚接到通知赶来。他说看首播时认出了小花的绣法,想起老师教过求救信号。”
小花抱着作业本欢呼,辫梢的红绳扫过桌面,碰倒了装玻璃珠的铁盒,珠子滚落一地,在阳光下闪得像星星。安欣捡起一颗蓝色的,正是灯明在竹筐里找到的那颗。
“安姐姐,我们明天还首播吗?”小花仰着脸问,手里还攥着那枚绣了求救信号的平安结。
“播。”安欣把玻璃珠放回盒里,“还要教更多孩子,绣出属于自己的光。”
窗外的野菊在风中轻轻摇曳,远处传来联防队的摩托车声,大概是送男孩去见父母。安欣望着屏幕上渐渐暗下去的“首播结束”提示,突然觉得这小小的屏幕像扇窗,一边连着村寨的土布和针线,一边连着无数双渴望安全的眼睛。而那些穿过屏幕的绣线,正悄悄织成一张网,把每个需要守护的孩子,都温柔地兜在里面。
第二天的首播,“星空下的守望者”没有再出现,但多了很多新ID,名字都带着“平安”“守望”“灯塔”之类的词。安欣教大家绣歪脖子树和玻璃珠,弹幕里有人说:“我要教会我女儿,让她知道,不管在哪里,总有人在找她。”
安欣看着那行字,低头在新的绣绷上落下第一针。阳光透过窗,在靛蓝的土布上投下小小的光斑,像极了那颗被找到的蓝色玻璃珠,也像所有藏在屏幕背后,未曾言说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