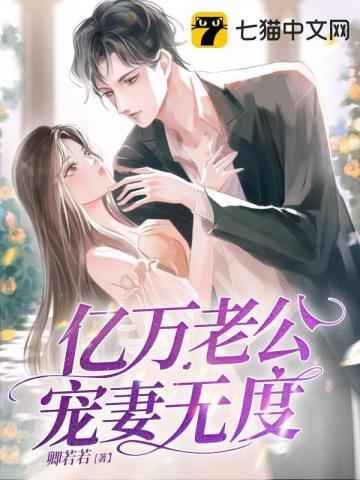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安史之乱占领了多少地 > 第63章 棋落无声血染春帖(第2页)
第63章 棋落无声血染春帖(第2页)
城中内应,不止七人,而是“内十三,外五”,共计十八名死士,皆是安禄山昔日麾下悍卒或受其恩惠的范阳商贾,只待时机一到,便在城内纵火、开门,与城外大军里应外合。
听完供述,侍立一旁的陈砚舟脸色煞白,当即请命:“将军,事不宜迟,请准许末将立刻带人全城抓捕,将这十八个逆贼……”
“不必。”赵襦阳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打断了陈砚舟的话,下达了一道让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命令,“不杀一人,不拘一众。派人潜入他们宅邸,将其私藏的所有兵器、甲胄、密信,尽数抄录绘图,而后原样放回,不得惊动分毫。”
“将军!”陈砚舟大惊失色,“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倘若他们明日午时真的在鼓楼举事,后果不堪设想!”
赵襦阳缓缓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任凭夹杂着冰晶的寒风灌入室内。
他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与未融的春雪,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等不到午时。真正的杀招,不在城内,而在‘信’。”
正月十西,天色未明。
薛七郎己换上一身风尘仆仆的商贾行头,脸上涂了蜡黄,眼神惶恐,怀揣着一份精心伪造的“密报”,在城门开启的瞬间,便策马疾驰,首奔范阳方向而去。
那份密报里,详细“记录”了恒州城防的致命漏洞,并“确认”了内应将于十五日元宵夜动手,届时可内外夹攻,一举破城。
三日后,这封信被呈到了安禄山的帅帐中。
其心腹谋主高尚展开信纸,只看了几眼,便抚掌大笑:“大帅,成了!恒州城内应己然备妥,约定十五夜举事,此乃天赐良机!”
安禄山一把夺过信,的身躯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他盯着信上那熟悉的暗记,眼中贪婪与暴戾之色尽显,猛地一拍帅案:“天助我也!传我将令,三镇兵马不必再等,全军提前一日发动总攻!就在今日,正月十西午时,踏平恒州,活捉赵襦阳!”
同一日的黄昏,恒州城头,风雪渐起。
赵襦阳亲手将那些从内应家中抄录来的密信原件,一封封投入火盆。
猩红的火焰舔舐着纸张,将那些罪证化为灰烬,只留下副本存入机要档案。
戚薇端着一碗滚烫的汤药走来,低声在他耳边道:“你算准了安禄山生性多疑又急功近利,必定会提前动手。可你这么做,等于亲手打乱了我军的布防节奏,将恒州置于更危险的境地,值得吗?”
赵襦阳没有回头,他接过药碗,一饮而尽。
苦涩的药汁顺着喉咙滑下,仿佛也无法驱散他眉宇间的寒意。
他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北方天际,那里,一缕极淡的狼烟正袅袅升起,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如同即将滴落的血珠。
“真正能打乱我的,从来不是叛军的兵锋,而是朝廷那迟缓到令人绝望的诏令。”他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风雪吞没,“安禄山早一日攻城,郭子仪的援军便能早一日得到确切军情,被迫加速行军。我宁可背上一个‘擅开边衅,违律失期’的罪名,也要为恒州,为整个河北,抢下这宝贵的七十二个时辰。”
话音刚落,远处,第二道、第三道叛军的烽火接连升起,连成一片,如同一轮血色的弯月,悬挂在恒州城的上空。
战争,以一种被他强行扭转的方式,提前降临了。
赵襦阳缓缓卷起手中那份早己烂熟于胸的《守城八策》,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喃喃自语,像是在对这满城风雪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春联己贴,刀己出鞘——这一局,该我落子了。”
他的目光从远方的烽火移开,缓缓掠过城墙下那一片片沉默的屋脊,最终落在了灯火最为稀疏的西坊一角。
夜色渐深,那里的黑暗仿佛比别处更加浓郁,也更加沉重。
他转过身,对始终立于身后的陈砚舟下达了今夜最后一道,也是最令人费解的命令。
“砚舟,传令下去。”他的声音平静无波,“让西坊各街口,把灯笼都挂起来。要最亮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