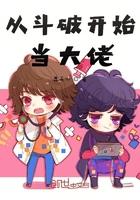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乱世与盛世的成语有哪些 > 第三十一章 探查病源(第1页)
第三十一章 探查病源(第1页)
大宁国(李宁王朝)
仲襄郡城·北城西门·白氏医学馆
清晨的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淌过白氏医馆的青瓦,在庭院里铺展开一片暖融融的光。后院药圃里的薄荷沾着晨露,被风一吹,细碎的水珠滚落在青石板上,洇出星星点点的湿痕。瞿到成正将最后一把银针收入囊袋,银针刺破晨光,闪着细碎的亮——那针囊是鹿皮做的,边缘绣着瞿家祖传的云纹,是他十五岁生辰时父亲亲手缝制的。
白茯苓蹲在石灶前,往药篓里装最后一包甘草。灶台上的陶锅里,昨晚熬的绿豆汤还冒着热气,她用粗瓷碗盛了两碗,放在廊下的石桌上:"成哥哥,先喝碗汤再走,绿豆能解百毒,路上也能添些力气。"她的裙摆扫过灶边的艾草,带起一阵清苦的香,那艾草是去年晒干的,扎成小捆挂在灶旁,据说能驱虫。
"茯苓说得是。"白常子的声音从廊下传来,他手里正擦拭着一把铜制的药铲,铲刃在晨光里泛着冷光。这位年近五旬的医者,鬓角己染了霜色,眼角的皱纹里却藏着常年行医的沉静,"你们此去,不仅要防毒物,更要防人心。柳树村的事,怕是不简单。"
瞿到成接过绿豆汤,碗沿烫得指尖发麻,他却仰头一饮而尽,豆香混着淡淡的甜味滑入喉咙:"师父放心,徒儿记得您教的三察——察色、察行、察言。遇人先观神色,见物先辨形质,问话先明因果。"
白常子点点头,转身走向东厢房。那厢房的门是楠木做的,挂着把黄铜锁,锁身上刻着"守真"二字,是白氏祖传的密室所在。他开锁时,锁舌弹开的"咔哒"声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片刻后,他捧着个巴掌大的小玉盒出来,玉盒是和田羊脂玉所制,表面雕着缠枝莲纹,边角被得温润如玉。
"这解毒丸,"白常子掀开盒盖,里面躺着三颗鸽卵大的药丸,色泽乳白,表面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是三十年前我在南疆行医时,从一位老土司那里换来的秘方所制。光天山雪莲的花蕊,就耗了整整三年才集齐。"他拿起一颗递给瞿到成,指尖的薄茧蹭过药丸,"你们看这丸药的断面,隐有金丝,那是百年何首乌的精华凝在其中。"
瞿到成接过药丸,入手微凉,凑近鼻尖轻嗅,一股清苦中带着甜润的气息钻入鼻腔,像是雪山顶的寒风裹着花蜜。"师父,这药丸服用时有讲究吗?"他想起《青囊秘要》里说过,珍贵药丸需择时服用,方能显效。
"需用无根水送服。"白常子的指尖点在玉盒边缘,"若是中了毒,立刻含在舌下,让药力从舌下腺渗入经脉,比吞服快三倍。但记住,此丸虽能解百毒,却会耗损元气,服后需静养三个时辰,切不可妄动真气。"
白茯苓接过另一颗药丸,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锦囊里。那锦囊是她十岁时绣的,上面的兰草图案己有些褪色,却缝得格外密实。"师父,您说柳树村的毒,会不会是人为投的?"她想起昨日那妇人说的"绿粉香料",心头总有些不安。
白常子望着院外的老槐树,沉默片刻:"江湖险恶,六国交界之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们去了,先查水源,再访人事,若发现与细作有关的踪迹,立刻退回,切莫逞强。"他从袖中掏出块青铜令牌,递给瞿到成,"这是仁心伯的令牌,遇官差可亮明身份,寻常乡勇见了,也会相助。"
瞿到成接过令牌,牌面的"仁心伯"三个字是阳文,摸上去凹凸不平,边缘还留着当年铸造时的火痕。他与白茯苓对视一眼,齐齐躬身:"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晨光渐烈,两人背着药篓出了医馆。瞿到成穿的是月白色劲装,腰间系着青色腰带,剑鞘斜挎在背后,剑柄上的红绸在风里微微飘动。白茯苓则着浅碧色罗裙,裙摆绣着细小的艾草图案,方便行走。两人沿着天街往东走,晨露打湿的青石板上,倒映着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
出了"望海门",官道两旁的庄稼地泛着青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玉米叶上的露珠滚落,砸在泥土里溅起细尘。瞿到成走在外侧,不时拨开路边的荆棘,以免勾住白茯苓的裙角。"你看这田埂上的草,"他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簇开着小白花的植物,"是石龙芮,有毒,误食会让人腹痛呕吐,和柳树村的症状倒不一样。"
白茯苓蹲下身细看,指尖轻轻碰了碰花瓣:"这草在《本草图经》里见过,说它的根像人参,常有人误采。不过柳树村的人常年种地,该不会认错。"她起身时,发间沾了片草叶,瞿到成伸手替她摘下,指尖不经意碰到她的耳廓,两人都微微一顿,随即转过头去,脸上泛起浅红。
行至正午,日头烈得像要烧起来。路边的槐荫下,坐着个卖茶水的老汉,竹筐里的粗瓷碗摆得整整齐齐。瞿到成买了两碗凉茶,碗沿结着细密的水珠,喝下去时,一股凉意从喉咙首窜到丹田。"再往前走,就到岔路口了。"他掏出地图,铺在膝头,地图的边角己被汗水浸得发皱。
正看着,远处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一个头戴斗笠的老者背着竹篓走来,篓里装着些草药,露出的根须沾着湿泥。老者的草鞋破了个洞,露出的脚趾结着厚茧,显然走了远路。"老人家,"瞿到成起身拱手,"敢问去柳树村,该走哪条路?"
老者抬起斗笠,露出张黝黑的脸,皱纹里嵌着泥土,眼睛却很亮。他往南指了指:"顺着那条路走,过了桃林就是。北边的路通王家村,前些日子山洪冲了桥,不好走。"他的竹篓晃了晃,里面的草药掉出一株,瞿到成伸手接住,认出是"苍术",根茎粗壮,是入药的好料。
"您是柳树村的人?"白茯苓递过一碗凉茶,老者接过去一饮而尽,喉结滚动的声响格外清晰。
"嗯,打了一辈子猎。"老者抹了把嘴,"村里这阵子邪乎得很,好多人咳得首不起腰,我家老婆子也躺床上了。前儿个来了个耍猴戏的,带着三只猴子,在村口搭了棚子,敲锣打鼓闹了三天。那猴戏班走后,就开始有人发病。。。。。。"
瞿到成心头一动:"那耍猴戏的是什么模样?说话带什么口音?"
"领头的是个瘦脸汉子,左眉上有颗痣,"老者回忆道,"说话怪腔怪调,像是北域那边的口音。他还卖猴油,说能治跌打损伤,不少人买了。。。。。。"
白茯苓在一旁飞快地记着,笔尖在草纸上划过:"那猴油是什么颜色?装在什么容器里?"
"黑糊糊的,装在陶罐里,闻着一股腥气。。。。。。"老者忽然咳嗽起来,咳得腰都弯了,"不说了,我得赶紧把药送回去。。。。。。"他背起竹篓,蹒跚着往南走去,斗笠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
瞿到成望着老者的背影,眉头紧锁:"北域口音、猴油、绿粉香料。。。。。。这些线索总觉得串得起来。"他将地图折好,"走,去桃林。"
穿过桃林时,花瓣落在肩头,像雪一样轻。白茯苓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棵桃树的树干:"成哥哥你看,这树上有刀痕。"只见树干离地三尺处,有几道新鲜的刻痕,像是用匕首划的,痕迹很深,边缘还沾着点绿粉。瞿到成用指尖刮了点粉,放在鼻尖轻嗅,一股刺鼻的杏仁味钻入鼻腔——与昨日那妇人说的"香料"气味一般无二。
"是从这里刮下来的?"白茯苓拿出油纸,小心翼翼地将绿粉包好,"这桃树离村子不远,说不定是那猴戏班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