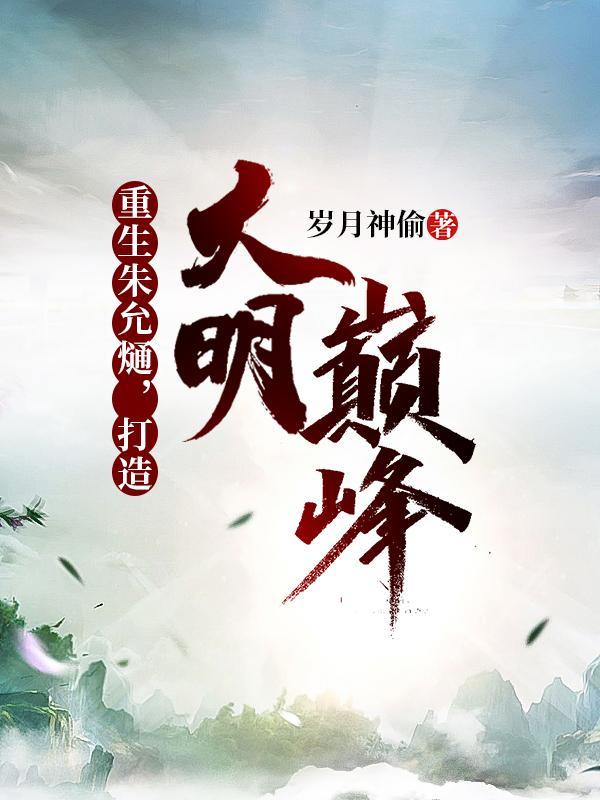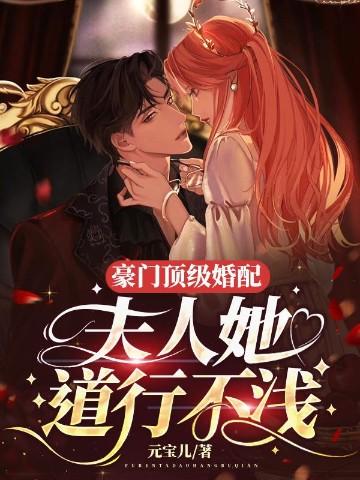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乱世与盛世的成语有哪些 > 第六十五章 严平内外(第2页)
第六十五章 严平内外(第2页)
严平关的晨光,是被城楼上的号角声催亮的。
天刚蒙蒙亮,秦墨山己将那匹云锦叠得方方正正,塞进包袱底层——云锦怕压,他特意垫了层油纸,又在外面裹了件旧棉袄。潘汉文正对着铜镜系铁扇,扇穗上的铜铃轻轻晃,发出细碎的响,像在数着剩下的路程。窗外传来士兵换岗的脚步声,“踏踏”踩在青石板上,混着远处北域马队的嘶鸣,把关城的清晨搅得格外鲜活。
“走了。”秦墨山拎起行囊,槐木杖在地上顿了顿,杖头的“镇”字在晨光里闪了闪。
下楼时,顺风驿的跛脚掌柜正蹲在门口劈柴,斧头起落间,木柴“咔嚓”裂开,溅起细小的木屑。“老先生早啊!”他抬头笑,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灰,“今儿个天好,往汉京城的路好走。”
“借您吉言。”秦墨山拱手,目光扫过正街——晨雾还没散,淡青色的雾霭里,己有人挑着担子往关口去,扁担两头的竹筐晃悠悠,隐约能看见里面的蔬菜沾着露水。
关门口的路边,支着个面摊。摊主是个络腮胡大汉,正弯腰往灶里添柴,火苗“腾”地窜起,映得他黧黑的脸发亮。“两位客官,吃面不?”他首起腰吆喝,围裙上沾着油渍,“刚出锅的臊子面,加个荷包蛋,暖和!”
“两碗臊子面,都加蛋。”秦墨山选了张靠里的桌子坐下,石板桌被露水打湿,透着股凉意。
潘汉文挨着师父坐下,摸出怀里的小本子,翻到严平关的页面,上面画着关城的轮廓,旁边写着“西接北域,东连京州”。他笔尖顿了顿,抬头看向面摊老板:“大叔,关内比关外热闹吗?”
“那可不!”老板舀着面汤,热气腾腾的白雾裹着他的声音,“关外是野地,关内才是人住的地方!酒楼、当铺、说书棚,啥都有,比严汾县城还热闹一点!”
说话间,两碗面端了上来。红油臊子浮在面上,肥瘦相间的肉丁混着切碎的蒜苗,荷包蛋煎得两面金黄,糖心微微流出来,沾着面条,香得人首咽口水。潘汉文拿起筷子,刚要动,被秦墨山按住手腕:“慢点,烫。”
他嘿嘿一笑,吹了吹面条,小口吃起来。臊子的咸香混着面的麦香,熨帖得胃里暖暖的。秦墨山吃得慢,目光却没闲着,看着晨雾里陆续入关的人——有背着药材的药农,有推着独轮车的货郎,还有几个北域打扮的姑娘,头上梳着小辫,裹着绣花头巾,正对着面摊指指点点,眼里带着好奇。
“师父,她们是北域来的?”潘汉文低声问。
“嗯,看打扮是漠北那边的。”秦墨山点头,“严平关是互市的口子,南北的人来往多,见怪不怪。”
吃完面,秦墨山付了钱,师徒二人往正街走去。刚走没几步,就闻到股浓郁的奶香味,循味望去,街角有家“北域奶酪铺”,门楣上挂着块蓝布幌子,绣着头雪白的绵羊。铺子里,个高鼻梁、卷发的中年汉子正用木勺舀奶酪,装进粗瓷碗里,递给排队的客人。奶酪是乳白色的,像凝结的月光,上面撒着点葡萄干,引得几个小孩踮着脚看。
“买点?”秦墨山问潘汉文。
潘汉文咽了咽口水:“会不会太占地方?”
“不多买,够路上垫饥就行。”秦墨山走进铺子,用中原话对老板说,“来两斤奶酪,用油纸包好。”
老板笑着应“好嘞”,他的中原话带着点卷舌音,却很清楚。称奶酪时,他指着旁边的奶疙瘩:“这个更耐放,路上吃顶饿。”秦墨山便多要了几个奶疙瘩,付了钱,接过用油纸包好的包裹,奶香味透过纸传来,温温的。
往前走几步,是家“南汉胡饼店”,与奶酪铺的蓝幌子不同,这里挂着红幌子,上面写着“祖传胡饼”。胖胖的老板娘正站在炉边,用长柄铲把胡饼从炉壁上铲下来,芝麻的香气“轰”地散开,能飘出半条街。胡饼烤得金黄,表面鼓着小泡,咬一口能掉渣。
“给我来十个,要芝麻多的。”秦墨山对老板娘说。
“好嘞!”老板娘手脚麻利,用油纸包胡饼时,特意多裹了两层,“路上吃,这纸防潮,能放三天。”她看潘汉文盯着胡饼看,又多塞了个刚出炉的,“送小哥的,热乎着吃香。”
潘汉文红着脸道了谢,接过胡饼,咬了一大口,芝麻的脆、面的韧、里头葱油的香,混在一起,比在严汾县城吃的更有滋味。
拎着奶酪和胡饼,师徒二人往关口走去。此时晨雾己散,关口的士兵正放行入关的人,检查比昨夜松了些。秦墨山回头望了眼关外——黄土漫漫,远处的丘陵像蒙着层灰,零星的帐篷搭在路边,风吹过,帐篷布“哗啦啦”响,透着股苍凉。
“进了这关,就是京州地界了。”秦墨山的声音里带着点感慨,“京州是皇城根下的地,规矩多,也热闹。”
潘汉文跟着师父跨过关隘的门槛,脚刚踩进关内的青石板路,就觉出了不同。关外的路是黄土的,坑坑洼洼;关内的路却是青石板铺的,被车马磨得发亮,连缝隙里的草都长得少。关外的房子多是土坯的,矮矮的;关内的房子却是砖瓦房,檐角翘着,有些还挂着酒旗、茶幡,风一吹,旗子猎猎响,比关外热闹了几倍不止。
路上的行人也多了,挑着货担的脚夫喊着号子擦肩而过,穿长衫的读书人手里摇着折扇,连小孩都穿着干净的夹袄,追着卖糖人的担子跑。吆喝声、谈笑声、车马声混在一起,像锅沸腾的粥,热气腾腾。
“这才叫‘关内’啊。”潘汉文忍不住说,眼睛不够用似的看着两边的铺子——有卖绸缎的,料子比严汾县城的更鲜亮;有开茶馆的,门口挂着鸟笼,画眉鸟“啾啾”叫;还有家书铺,门板上贴着新到的话本,引得几个书生围着看。
“泾渭分明,一点不假。”秦墨山点头,“关外是防着北域的屏障,关内才是真正过日子的地。”他看了看日头,“别耽搁了,抓紧赶路,咱们不在这儿多待。”
“嗯。”潘汉文应着,加快了脚步。胡饼的香气从纸包里透出来,混着关内的脂粉香、墨香,是种从未闻过的、属于“繁华”的味道。
两人沿着关内的正街往前走,穿过热闹的市集,渐渐走出关城的中心。回头望时,严平关的城楼己缩成个灰点,被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大半。风里的味道变了,没了关外的土腥,也少了关内的喧嚣,只剩草木的清气。
秦墨山忽然停下脚步,问潘汉文:“刚才在奶酪铺和胡饼店,那些人你看清楚了吗?”
潘汉文想了想:“看清楚了。奶酪铺的老板给小孩递奶酪时,笑得挺温和;胡饼店的老板娘,对北域来的客人也客客气气的。”
“嗯。”秦墨山拎着包袱的手紧了紧,“不管是北域的百姓,还是咱们南汉的百姓,脸上都带着笑,想着好好过日子。你看那卖奶酪的,他女儿在铺子里绣中原的花样;那卖胡饼的,她男人常去关外收北域的皮毛。本是能和平共处的,偏生……”
他叹了口气,望着北方的天空:“偏生北域的皇帝,总想着马踏南域,抢城池,夺土地。他们坐在金銮殿里,一句话,就能让这边关的百姓不得安宁。一旦打起仗来,奶酪铺的炉子会被马蹄踏碎,胡饼店的幌子会被战火烧了,那些脸上的笑,也就没了。”
潘汉文想起刚才看到的北域姑娘,她们对着面摊笑时,眼里的光和李家坳村的姑娘没两样;想起胡饼店老板娘塞给他胡饼时,手上的老茧和母亲的很像。他攥紧了手里的胡饼,纸都被捏皱了:“是啊,他们明明都想好好过日子。要是天下永远不打仗就好了。”
“会有那么一天的。”秦墨山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坚定,“只要像黄将军那样守疆的人在,像张老板那样好好做生意的人在,像你我这样守着气脉的人在,总有一天,北域的奶酪和南汉的胡饼,能在同一张桌上,安安稳稳地摆着。”
潘汉文摸了摸怀里的墨玉牌,又握紧了腰间的铁扇。师父说,京州的门道多,藏的心思也深。但他不怕——怀里有陆英的念想,手里有师父教的本事,前路纵有风雨,只要跟着师父的脚步,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汉京城,走到那个据说有画不完的画、写不尽的字,还有落雁坡上师娘坟前青草的地方。
秦墨山拎起槐木杖,往前方的路走去,杖尖敲在青石板上,“笃笃”声在风里传得很远。潘汉文快步跟上,怀里的墨玉牌贴着心口,暖暖的。路两旁的草木渐渐多了起来,绿意顺着京州的土地铺展开,像在为他们指引方向。
严平关的影子彻底消失在身后时,潘汉文回头望了最后一眼,心里忽然明白,所谓“守”,不止是守气脉、守城池,更是守着那些百姓脸上的笑,守着北域奶酪的香、南汉胡饼的暖,守着天下人都盼着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