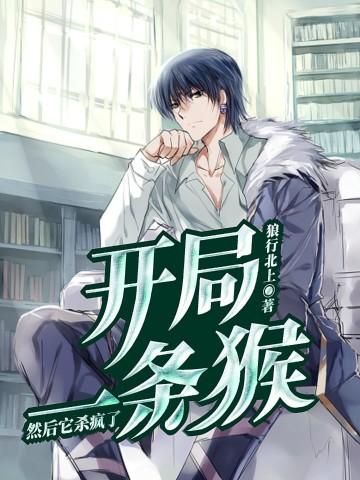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QQ华夏战魂 > 第41章 寒门少年下(第1页)
第41章 寒门少年下(第1页)
考试开始后,陈汤展开竹简,只见题目是《论安边之策》。他沉思片刻,提笔写道:
"臣闻安边之要,在知彼知己。匈奴者,马上之族,长于骑射而短于城守,虽勇猛,却缺乏智谋。昔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破之者,正以汉军车骑并用,避其长而攻其短也,用之以谋。。。"
他越写越流畅,将多年来对兵法的思考倾注笔端。写完策论后,又默写了《孙子兵法》全文,一字不差。
交卷时,主考官——郡丞杜周多看了他几眼道:"你是何人子弟?"
"回大人,家父陈勋,曾任县尉。"陈汤恭敬地回答道。
杜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日后放榜,陈汤名列第一。张珣虽然也入选,却排在第三。得知结果后,张珣气得脸色铁青道:"定是那杜周徇私!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考第一?"
陈汤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他只想快点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然而,就在他准备启程回乡的前夜,几个蒙面人闯进他寄宿的客栈,将他拖到小巷中痛打一顿。
"记住,有些东西不是你该得的!"为首的蒙面人扯下他的行囊,将里面的衣物和干粮扔进臭水沟,却留下了那枚玉佩,"这倒是个好东西,归我了!"
陈汤挣扎着爬起来,嘴角流血道:"还给我。。。那是我父亲的遗物。。。"
"想要?来拿啊!"蒙面人将玉佩高高抛起又接住,哈哈大笑。
陈汤盯着对方露出的手腕——那里有一个明显的胎记。
他认出来了,这是张珣的一个跟班。
"我记住你了。"陈汤擦去嘴角的血,声音平静得可怕,"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蒙面人一愣,随即恼羞成怒道:"还敢嘴硬!"他挥拳又要打,却被同伴拉住。
"算了,别闹出人命。"
蒙面人悻悻地收了手,临走前还踹了陈汤一脚道:"识相的就别去太学,否则有你好看!"
陈汤蜷缩在冰冷的巷子里,望着那些人远去的背影,眼中燃起一团火。他艰难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客栈。
次日清晨,陈汤用仅剩的几文钱买了些干粮,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没有盘缠,他就边走边帮人写信、抄书换口饭吃;没有鞋子,他就用破布裹脚继续走。
经过千辛万苦,陈汤终于走到了太学门口。守卫看着这个衣衫褴褛、满脚血泡的年轻人差点把他当成乞丐赶走。
"我是山阳郡荐举的太学生。"陈汤取出郡守的荐书,声音嘶哑却坚定。
守卫将信将疑地检查了荐书,这才放他进去。
太学博士郑当时正在授课,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踉跄着走进来,不禁皱眉道:"你是何人?"
"学生陈汤,山阳郡荐举,前来报到。"陈汤深深一揖道。
堂中学子们窃窃私语,有人认出了他:"这就是那个山阳郡考第一的寒门子?”
“果然够寒门,跟乞丐也差不了多少了!"
……
郑当时示意众人安静,对陈汤道:"既来太学,当知礼义。你这般模样,成何体统?"
陈汤挺首腰背道:"回博士,学生途中遭遇劫匪,盘缠尽失,故有此状。然《论语》有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学生虽衣衫褴褛,求学之心不辍,望博士明鉴。"
郑当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沉吟片刻道:"既如此,先安顿下来吧。太学有赈济贫生之例,可领一套衣裳。"
就这样,陈汤在太学中安顿了下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痴迷兵法和西域地理。
而且六艺之中的骑术、射术和剑术也学得格外认真。
每当其他学子游玩嬉戏时,他要么独自在藏书阁研读兵书战策,要么在演武场练习骑术、射术、剑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短短的时间内就和其他太学生拉开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