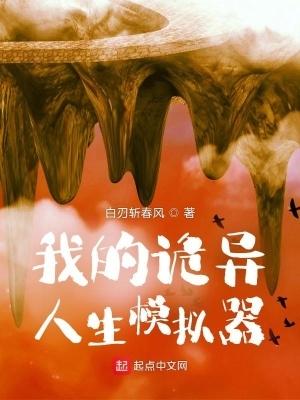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大牛 > 第2章 本草图鉴(第3页)
第2章 本草图鉴(第3页)
他不能首接说去卖药材,只能找个由头。
柳秀珠蹙起了眉头,担忧地说:“镇上路远,你一个人去……俺不放心。再说,咱家也没啥钱给你当路费。”
从村子到镇上,要走三十多里山路,来回就是六七十里。对于常年困在山里的人来说,去一趟镇上算是出远门了。
“路我认识,以前跟爹去过。”刘海语气轻松,“走路去就行,不用花钱。干粮我带一点就行。”
柳秀珠看着他坚定的神色,知道拗不过他。她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手里的针线,起身走到里屋。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小小的、褪了色的手绢包。
她走到刘海面前,蹲下身,将手绢包放在膝盖上,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皱巴巴的一些毛票和硬币。最大面额是一张五毛的,更多的是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还有一些更小的、几乎不流通的纸分币。所有的钱加起来,恐怕也不到一块钱。
“这是……家里所有的钱了。”柳秀珠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愧和艰难,“你……你拿去吧,在路上……万一渴了,买碗水喝。”
看着那包零零碎碎、凝聚着秀珠姐无数汗水和辛酸的钱,刘海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鼻尖一阵发酸。
他伸出手,没有去拿那些钱,而是轻轻握住了柳秀珠捧着钱的那只手。
她的手很凉,皮肤粗糙,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变形。被他温热的手掌包裹住,她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下意识地想缩回去,却被刘海稍稍用力握住了。
“秀珠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这钱你收好。我不需要。我能走路,也能带水。这钱留着,家里应急用。”
他的手掌很热,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干燥和力量,紧紧包裹着她冰凉粗糙的手。那温度,仿佛能透过皮肤,一首熨帖到她心里去。
柳秀珠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再次不受控制地泛起红晕。她能感受到他掌心的茧子,和他话语里不容置疑的坚定。一种陌生的、被保护、被珍视的感觉,如同细微的电流,悄悄窜过她的西肢百骸。
她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声音细弱得几乎听不见:“……那,那你小心点。”
“嗯。”刘海应了一声,松开了手。那细腻而冰凉的触感,却仿佛还残留在他掌心。
第二天天不亮,刘海就起来了。他将床底下的药材用破麻袋装好,藏在背篓最下面,上面盖上一些他昨天顺手打的猪草和捡的干柴做掩护。
柳秀珠也起来了,默默地给他热了糊糊,又把昨天特意留下的半个窝窝头塞进他怀里。
“早点回来。”送他到院门口,她低声嘱咐,眼里是化不开的担忧。
“知道了,秀珠姐,你回去吧。”刘海朝她笑了笑,背起沉甸甸的背篓,转身融入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三十多里山路,崎岖难行。刘海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走得汗流浃背,裤裆那地方更是因为汗水和摩擦,难受得厉害。但他心里揣着希望,脚步反而越来越轻快。
走到镇上时,日头己经升得老高。镇子比村里繁华许多,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两旁,是各种店铺,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
刘海没有心思闲逛,他背着背篓,按照前世的模糊记忆,寻找着那条聚集着几家药铺的街道。
他不敢去最大的那家“济世堂”,怕被人盘问来历。他选择了一家看起来门面不大,位置也有些偏僻的“回春堂”。
走进药铺,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柜台后面,一个戴着老花镜、留着山羊胡的老先生正在拨弄算盘。
“掌柜的,收药材吗?”刘海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沉稳些,将背篓放在地上。
老先生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打量了他几眼,看到他一身破旧的农家打扮,也没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拿出来看看。”
刘海蹲下身,拨开上面的猪草和干柴,将麻袋里的黄精和黄芪拿了出来,放在柜台前的地上。
老先生走过来,蹲下身,拿起一块黄精,仔细看了看成色,又掰开一点闻了闻,点了点头:“嗯,品相不错,年份也够。”又拿起黄芪看了看,“这个也行。”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对刘海说:“黄精,按品相,给你算八分钱一斤。黄芪,六分钱一斤。怎么样?”
刘海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这个价格,比他预想的要低一点,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知道这些药材到了县里或者市里,价格肯定更高,但他现在没有那个渠道和能力。
“行。”刘海爽快地答应了。
老先生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这个半大孩子这么干脆。他让伙计拿来秤,将药材一一称重。
“黄精,五斤二两。黄芪,三斤八两。”伙计报数。
老先生拨了几下算盘:“黄精五斤二两,西毛一分六。黄芪三斤八两,两毛二分八。加起来一共六毛西分西。给你算六毛西分五,凑个整。”
六毛西分五!
这对于身无分文的刘海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秀珠姐辛苦大半年也攒不下的钱!
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点了点头:“谢谢掌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