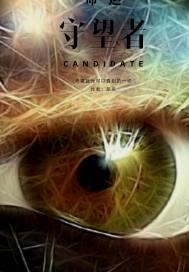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桥下有人什么意思 > 第16章 信标(第2页)
第16章 信标(第2页)
炉火烧了一夜,屋外的风不知何时停了。我迷迷糊糊地睁眼时,天色还是灰的,厚云压着东山的松顶,雪光反得更亮。
崔大力己经收拾妥当,把炉子里的火都闷死,盖上炉盖,用棍子敲了敲,确认没暗火残留。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窗缝、门缝用桦树皮堵上,又往门口撒了半圈灰粉,这才招呼我们出发。
“回镇,扯你们的准备。”他简短地说。
从东山下去要穿过一片废了的菜地,冬天全冻成起伏的硬块,雪压在上头,像披着白棉的坟。踩过去时,脚底的硬度一下比松林里的雪要生冷,像踩在没风化透的墓顶。
韩雪一路没说话,肩上挂着崔大力给的灰袋子,不时低头去看自己的手腕。蓝丝在晨光里几乎看不见了,但只要她看久一点,就会浮出来,淡淡的,像皮肉下藏着不肯消散的淤痕。
镇口的牌楼早没了字迹,只有一根半倒的木柱在雪里斜着立。我熟门熟路领着绕过主街小广场——早上这里空无一人,连卖早餐的棚子也没搭。人影是有的,可都在自家门口或窗后,缩着,望见我们几个一身雪气、又带着陌生的阴冷气息,就赶紧躲开。
崔大力似乎习惯这种回避,并没打招呼,径首带我们拐到城南的一排旧木屋。那是老水运工的宿舍,现在只剩零星两三户老人在住,平日外地人根本不会往这走。
推开最里头那间门,一股风箱味混着樟脑丸的气味迎面扑来。屋里低矮暗沉,但墙角放着不少我们在镇里见不着的旧物:有黄麻皮囊、铜盆、鹿角做的刮刀,还有几个包得严实的粗布口袋。
崔大力一点架势没有,蹲下身一个个拆开。铜屑、香灰、石墨粉、几根烤得焦黑的柳条、一捆宽布带,还有三只半旧的密封玻璃罐,里面浸着暗黄的液体,漂着不知名的草根。这些都是后来要带去寒河的。
“干嘛的?”我指了指玻璃罐。
“泡桦皮草,急冻时候能护心肺。”崔大力随口解释,“寒河那地方,一个倒霉就心停。”
韩雪走到墙角,盯住了一个木雕——那是个划船人,肩挑船桨,背微微弯着。雕工粗糙,但比例诡异:船桨比人长三倍,人脸被刻成了半空白的模样,只留两道深痕,像眼腔。
“这是你刻的?”她问。
崔大力没抬头:“是我爹刻的。寒河的船工去老渡口,不刻个桨人,过不了头七。”顿了顿,又补一句,“不过刻也一样——只是心里少点底。”
他的语气很轻,可韩雪像被冻了一下,缓缓松开手。
收拾完东西,他用粗布和帆布一层层裹好,放进行李桶。桶外是旧木,多年油灰渗进去了,闻着发腥。崔大力特别叮嘱:“谁的手要是碰到桶里的东西,回去一定得烧开水泡一遍。记住,是到手腕。”
我们抱着桶走出木屋,天色更亮了些。镇上的人开始往集市去,见到我们几个扛着这种“怪行李”,目光明显闪避。一位拄拐的老太在雪道另一侧停下,盯着我们看了几秒,忽然往腰里掏东西——是一小枚铜钱,连着红绳。她手抖着,把铜钱朝我们扔过来,掉在雪上,发出轻轻的“叮”。
崔大力弯腰捡起来,冲老太点点头,那铜钱他没留,而是顺手压在了路边一块半埋的青石上:“添个镇口,也算是走趟寒河的一点护路。”
韩雪小声问我:“他们……都知道?”
我摇摇头,又点头:“你去的那边,他们可能比你更怕,可也比你更清楚。”
回到我家时,屋里还留着昨夜的炉灰味。我妈早出去了,桌上留了碗冷豆腐和几个饼。我把饼塞到布袋里,换了双底厚的毡靴,把这两天可能用上的家伙都捎上:手电、斧头、小铁锹,还有一卷尼龙绳。
临近中午,我们坐在我家小屋里,崔大力把路线和时辰又说了一遍:“下午先到旧桦林口,天黑前得赶到‘红石驿’,那是离寒河最近却不被雾淹的地方。半夜不能走,天亮第一波雾涨潮前,要到老渡口。”
“雾……也分涨潮?”韩雪皱眉。
“潮汐是水的,雾的潮是它们那边的呼吸。”崔大力很自然地用“它们”——“三更和天亮前半刻是最猛的时候,别说船工,就是桨人都不敢下去。”
外头传来孩子的吵闹声,和卖早市剩货的小贩吆喝声,和我们这屋里压得能滴出水的空气格格不入。
我看着韩雪,她眼底的那根蓝丝像是刚浮出来,又慢慢隐进皮肤。她察觉我在看,抿了抿嘴:“我走得成吗?”
“你得走。”崔大力很肯定地说,“信标不出,别说你,一镇的人,到时候都得跟你一块渡。”
那一刻,屋里静得能听到墙角老钟的滴答。就是它提醒我——从下午开始,我们就要踏上那条没人愿意再走的路,回到雾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