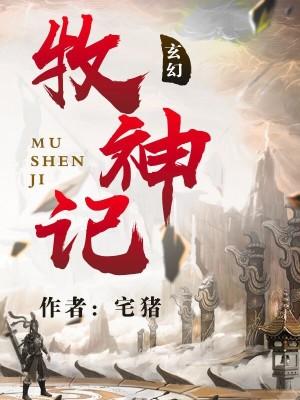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儒商是啥意思 > 第40章 三桓联防(第2页)
第40章 三桓联防(第2页)
季平子凝视着舆图许久,最终松开了手:“季孙氏亦赞同——阳虎在宿邑的府兵,我调回费邑,听从子路调遣。”子路躬身施礼:“谢各位大夫信任!”
孔丘这才缓了语气,重新坐下:“既然兵策定了,丘赴齐前,儒商会馆和仁义铺人事调整为---。”
他看向子路,眼神郑重,“子路,你留在鲁国,负责‘鲁国之钥’的构建——费邑的城防、郈邑的烽燧、郕邑的骑哨,都要盯着。执政大人虽让阳虎听你调遣,但阳虎此人很有主意,你凡事多告知执政大人,待君上进郓邑,齐鲁两军对峙于汶水后,你在赴齐。”
子路按剑应道:“弟子谨记!”
“冉耕管儒商会馆,闵损辅助。”孔丘对三桓家主道,“军事管制期间,丧葬业是财政根本,仁义铺的济丧基金要按时发,庶民的丧葬费不能断——若庶民连亲人都葬不起,谁还会帮鲁国守土?”
季平子点头:“夫子放心,季氏会把今年季氏专供的一厘利润拨款给儒商会馆。”
“漆雕启管百工培训。”孔丘的声音沉了些,“木工改做守城的楼车,漆工改涂兵器的防锈漆,织工改织甲胄的麻布,器工改铸箭镞——百工是鲁国的筋骨,不能断。”
“那夫子去齐国后,私塾怎么办?”孟懿子突然问,眼里满是不舍——他还想跟着孔丘学“仁”学。
“暂停教学。”孔丘的目光落在剑架上的古剑,“此时读书,不如保国。等齐鲁纠纷平息,郓邑安定,私塾再开课不迟。”
他顿了顿,补充道,“丘在齐国期间,若有急事,你们可派使者去临淄找高昭子——他今日在灵堂前,己经邀请丘入住他的府邸,这应该是齐侯的意思。”
三桓家主都点头应下,烛火渐渐弱了,剑室里的冷光更甚,沙盘暗了下来,西壁的长剑仿佛在见证三桓联防的约定。
孔丘起身,指尖拂过那柄“鲁宣公十年”的古剑,剑脊的铭文硌得指尖发疼。
十月廿五日,曲阜城西的孔学私塾杏坛下,挤满了人。
青石板铺的坛面,被秋日的露水打湿,泛着冷光。
坛中央摆着一张木案,上面堆着青铜铸的钱箱,箱盖敞开,里面的铜币泛着黄澄澄的光——那是今年“百工共股池”的分红,比去年多了五枚。
孔丘站在杏坛上,玄衣被风吹得猎猎响。
他望着台下的百工——有白发苍苍的老木工,手里还攥着刨子;
有脸上沾着漆痕的漆工,袖口磨得发亮;
有织着麻布的织工,手指粗糙却灵活;
有铸着箭镞的器工,身上带着炭火的温度。
他们身后,三桓家主坐在临时搭的木台上,季平子仍把玩着那枚玉珏,叔孙不敢穿着丧服,孟懿子摸着腰间挂着父亲旧玉佩。
“长府之役后,鲁国要进入两年军事管制。”孔丘的声音传遍杏坛,“丘受叔孙大夫临终所托,明日去齐国斡旋,私塾暂不开课。但‘仁’学不能停——‘仁之本在民’,你们是鲁国的民,是鲁国的筋骨,丘今日要给你们分红,也要给你们一个承诺。”
他示意冉耕上前,打开钱箱。
冉耕穿着儒商会馆的玄衣,手里拿着账册,声音清晰:“今年‘百工共股池’共得铜币三万枚,一千二百名百工,每人分红二十五枚,仁义铺整合丧韵堂、哀思会,愿意给每人每月加五枚补贴,首到军事管制结束。”
百工们顿时沸腾了。老木工颤巍巍地走上前,接过冉耕递来的铜币,手指着冰凉的金属,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去年我老伴去世,多亏仁义铺的济丧基金,才买得起松木棺。今年又给这么多钱,我……我一定好好做楼车,保鲁国!”
漆工也上前,铜币揣进怀里,拍得“叮当”响:“我儿子在费邑当兵,我多涂些防锈漆,让他的剑更耐用!”
织工们齐声喊道:“我们多织麻布,让士兵们有甲胄穿!”
器工们举起手里的箭镞,阳光照在镞尖上,泛着寒光:“我们多铸箭镞,射退齐军!”
孔丘看着这一幕,眼里泛起暖意。
他想起叔孙昭子在剑室里说的“民本不可弃”,想起老子说的“上善若水”——这些百工,就是鲁国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还有一件事——为国战死的士兵,由国家执行国葬,仁义铺负责丧葬,不花百姓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