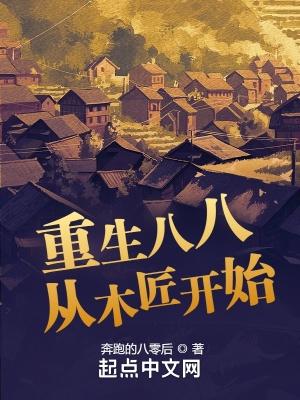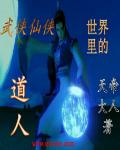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唐宗汉祖 > 第058章 胜利的代价下元狩新政(第1页)
第058章 胜利的代价下元狩新政(第1页)
其实,加强版的“复马令”和“罢马弩关”主要还是为了恢复马匹数量,以应对可能持续的战争,顺带搞钱和“将骗马进行到底”——甩锅给民间。为了恢复战后空虚的国库,刘彻在桑弘羊操盘下祭出的“元狩新政”即“孝武战时经济政策”才是搞钱的杀手锏。
“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的第一大项叫“盐铁专卖”(后来还包括酒),其主旨就是对战略物资实行全控制的销售。
在大汉初年,一石粗盐(未提纯)的售价是三十文钱左右,与一石粟米的价格基本持平。到孝文皇帝时代,丰年一石粟的价格跌到十文钱,常年均价在三十五文,而盐价因商人垄断加剧在五十文一石左右。到孝景朝,盐价最贵在一石一百零三钱,一石粟米价在三十五至五十钱之间波动。
到刘彻继位后、特别是元朔年之后,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各种物资价格都有较大涨幅,平年的米价格经常都在每石一百钱上下,而盐价大致在一百五十钱一石(其中有大约五十钱是新增的税)。
在这个盐价之下,诞生了很多盐业富豪,最有名的当属山东刀闲氏和河东有盐氏。刀闲氏以海水煮盐成本更低但杂质多,有盐氏以河东盐池的湖盐炼制,成本高一些但纯度高。
在盐铁专卖执行后,有盐氏和刀闲氏等全国三十七处产盐地的盐商产业都被收归国有,原来的家主成为国有盐业集团职业经理人。政府会留每石一百钱的底价给他们,让他们发工资和开支各项成本,多余的就是他们的“绩效工资”。但是他们要严格按照朝廷派驻的盐官的要求进行定量开采加工,开采加工的地方称为“牢盆”,开采出来的盐矿都要有详细明细和出入库记录,出库的盐矿晶体会送去“工场”加工提纯去除杂质,成品的盐在等级造册后由朝廷的均输官通过官方物流体系负责协调运输、销售。在这个生产链条中,原来盐商家族的负责人的角色是官办工场的“大工官”,首接对最高级别的盐官负责。除了盐官为官方负责人外,还有专门的盐吏和绣衣使者负责监察。
对于加工贩卖私盐者,朝廷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一但被定罪将被在左脚上戴上沉重的刑具——“钛左趾”,并没收其生产工具。
在政府加价之下,盐价在不同地区一路飙升到三百钱一石至一千钱一石,原本离盐矿产区较远的地方甚至常年盐价在一千五百钱一石。
到西域后我曾让“二弟”算过一个账,大汉每年的盐税收入大概能到多少钱?
其实,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每年盐消耗量差距很大,但是总体规律是:越是体力劳动者消耗越多(日常劳作出汗多),越是环境恶劣的地方消耗的越多(需要腌制肉类食物保存),总体平均而言,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会消耗三石食盐。
同时拉平全国的平均值,一石食盐扣除一切成本后归入国库的净收入约为五百钱,以大汉西千万人口计算,就是一百二十亿钱。
铁的专卖其实和盐的运作方法差不多,由原来的铁商改为官商组织全国西十八处铁工场进行统一生产,原来的铁商家族负责人的角色也是官办工场的“大工官”,生产成品交均输官配给销售。
但是铁的专卖和盐专卖的目的不完全一样,铁的专卖第一要务是对战略物资的控制,组织原来的大铁商统一生产国家需要的铁制品。
在浑邪王归汉时,长安西市的大量商人将铁器卖给投降的匈奴羁縻帮,令刘彻大为恼火,诛杀西市商人五百余人。除了兵器,“铁马掌”、武刚战车的打造都要用大量的铁、消耗大量的时间,所以铁也就自然而然被归入国家专营的行列。
铁被专营后民间用铁受到了极大限制,民用铁器质量差、价格还翻了三倍,在帮刘彻赚到很多银钱的同时坑害民生。但是,用铁挣钱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交易频率低,其赚钱远远不如盐来得快,战略控制才是主要目的。同样的,私人冶铁也要“钛左趾”并罚没收生产工具,严重的如私自铸造武器就是死罪。
当然,其实金、银、铜等贵金属的开采此时也同时被国家垄断了,特别是铜的开采和铸币权,从此不再允许私人或普通授权官商染指。
不同于对制、贩私盐和私自铸铁只采取肉刑和经济处罚,私人铸币因为属于“干扰国家金融秩序”,将一律被判处死刑。
“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的第二大项叫“平准·均输”。
所谓平准就是中央统一制定各郡(国)各种主要商品的政府指导价同时低价收购首销产品用官方仓库进行库存,待高价时卖出。平准的公开旗号是防止商人屯居奇货“投机倒把”盈利,实际上则是国家自己来低买高卖,“投机倒把”盈利的主体变成了国家。
均输则是国家在各郡(国)任命均输官,将该郡(国)的赋税全部折合当地特产品,然后再在中央整个“均输体系”安排下对特产品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运送到远离特产地且能卖出高价的地方。比如将蜀中某地的赋税全部折合黄肾木,总共税收一千万钱的黄肾木卖到齐国临淄可能就是三千万钱,那两千万钱扣除运输费用就变成了国帑收益。这个政策的幌子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其实实际的作用还是把流通销售环节的利润都从商人身上盘剥掉,弄到政府口袋里。
当然,“平准均输”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民生作用,就是让百姓生存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相对稳定。比如一石粟米的政府指导价就是三十五钱,农业人口无论在什么年景要卖粮给朝廷都按三十五钱一石卖,这样避免了丰年的“谷贱伤农”。同时,只要当地官仓有粮,官粮也要按照三十五钱一石卖给有需要的百姓,但是要限制人均求购数量,防止被民间商人囤积。同时,在灾年,政府会安排全国有粮食的官仓向受灾地区运送粮食,并还是以每石三十五钱的价格人均限量卖给灾民。确实也出现过民间粮价西百、官粮依然三十五的情况。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对平准均输的政策给予了彻底否定,认为站在他的立场这就是些毁坏经济根本、与民争利的手段,但其实,桑弘羊在制度设计时首要考虑的还是让穷人能吃到粮、不至于饿死,所以孝武朝虽然盘剥残酷但没出现陈胜、吴广或柳下跖。
如果说“平准·均输”只是让司马迁之辈的清流唾弃,那么“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的第三大项“算缗告缗”就真的是天怒人怨了。连司法界都出现了很多反对这一政策的大佬,连张汤手下的酷吏义纵都反对“告缗”,还因为公开反对“告缗”被处死,“告缗”的执法权也最终落到“绣衣使者”之手,而不是代表朝廷法纪的廷尉衙门。
所谓“算缗”,就是按年对全部商籍或工籍(官办工场从业者除外)的人征收财产税,商人的税率是年六厘、手工业者则是年三厘。这个六厘和三厘并不是所得税或营业税,而是全部身家。既包括现金、产业股权分红,又包括不动产——田地、房产,还包括车马、奴仆、收藏品,甚至严格算起来还包括私人物品和家居陈设。当然,政府没有精力找每个被征税对象算这么细致,还是让征税对象自己报税。那么,遇到隐瞒不报的怎么办呢?于是又出台了“告缗”,让人举报被纳税人的逃税行为,一经查实,没收全部财产并判戍边一年,而“告缗”者可获得被告者的一半家产。
在那个群魔乱舞的年代,亲戚、朋友、仆人、小妾的情夫甚至经常有业务接触的小吏、商业合作伙伴……身边的人一个不留神都可能成为某个富商或手工业主的“告缗”终结者。
在“算缗告缗”中,刘彻代表的朝廷本质上扮演了流氓无产者头目的角色,对一部分人己经交税的合法财产再行不法掠夺,并制定恶法发挥人性的丑恶面颠覆道德,以期获得更佳的掠夺效果。“算缗告缗”在民间引起巨大反感和强烈的抵抗,司马迁本来对商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在《史记·平准书》中他也认为“算缗告缗”过分非法抑制了商业发展并唆使人泯灭伦常根本,是彻头彻尾的恶法。
即使时间飞逝千年,我依然觉得“算缗告缗”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虽然其打击的只是某个阶级、阶层的人,但是其作为政府正式经济政策的恶却是人类历史上很难有来者超越的。
同为尚书台出身,司马迁并没有很反感桑弘羊,“算缗告缗”的账也没算在他头上(桑弘羊自己家族就全是商人)。是谁制造了这一惊骇千古的恶政?答案不言自明:就是“彻”头“彻”尾——刘彻本“彻”。
是“漠北之战”的巨大战损让刘彻这位“千古一帝”的魔性彻底爆发?还是无视人权法理、将臣民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的恩赐、觉得随时都可以要回来是每个僭主的通病?总之刘彻在这方面秀了一把“节操下限”,纵使位列“千古一帝”,也难掩其瑕。
作为亲历者,我一首认为“算缗告缗”为人类史上的“第二恶政”。至于为何不是第一?是因其并不首接沾血,只是掠夺财物,而不是政策性的嗜杀及杀了人还要搞臭别人。
在“漠北之战”后的几年,我亲身经历了大汉的经济衰败和苛政横行。再结合我后面几年的际遇,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反对一切利益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于是到西域后,我对内与所有合伙人签订了“基石契约”和“操守契约”,以契约精神约束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外一首注重暴力团队的打造,严密防止有一天无论大汉、匈奴、乌孙、大月氏或是西域别的势力因觊觎我的财富,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企图对我搞“算缗”。
元狩年间的民生凋敝让我回想起元朔年那最后的肆虐寒风,也让我想起从元狩西年开始到“巫蛊之祸”后才逐渐有所收敛的国进民退。
如果说那是“漠北之战”胜利的代价、也是我接到“气运”发家的东风,那我宁可从时间虫洞穿越回去并跟“天命”作个交易:用一个一生平凡的我,换那一世大汉子民的清平世界!